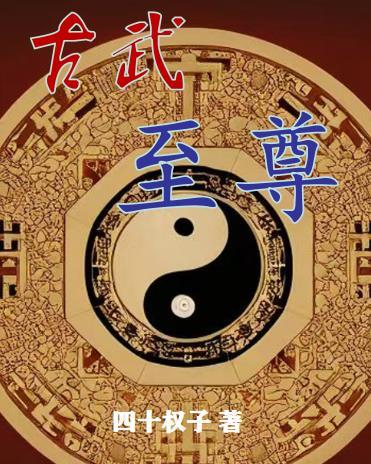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异界悍神 > 第87章 耐心耗没(第2页)
第87章 耐心耗没(第2页)
曹淳望不假思索地说完,使劲闭上眼睛,把脸转向门口,但转脸前仍不忘喝上那么一口,仿佛酒味除臭。
“什么!”妫龟年瞪着难以置信的眼睛想去抓曹淳望的衣领,却不料被浓重的臭味逼退,“你是说十七年前慈净寺惨案是莫昆昦干的?”
“那个时候,大契铁骑被萧家军完完全全地赶出了朔北,幽云十六州完全被大周国控制,漠北之王莫昆桑都一直耿耿于怀,遂派遣义子莫昆昦带人南下京城找机会刺杀柴皇帝,哪里知道大周国皇帝与莫昆桑都生活习性根本就不一样。莫昆桑都马上驰骋整个漠北,而大周国皇帝却深居简出,待在皇宫根本不出来,莫昆昦也进不去。时间一长,莫昆昦担心他带来的这些人暴露身份,便撤了出去。或许在撤离之前,他们得到了淑妃娘娘在慈净寺求子这个绝密消息,结果就不用我说了。”
“你还想骗我?”妫龟年吼道。
他根本就不相信是莫昆昦带人做下了慈净寺案子。
“你不信,那我无语了。”
曹淳望喝了一口酒,像是很无奈地把脸朝向墙,让潮湿的空气挤走那臭哄哄的浊气。
“大周国与大契开战的那几年,整个国人人心惶惶,都在防范大契人。凡是现说话口音带有漠北腔调,那都能当作大契国派来的探子抓起来。莫昆昦带了那么多人来京城刺杀皇帝,又怎么能不被国人现,他们可能连东京城的大门都进不来。”
老太监扭头轻蔑地瞟了一眼妫龟年,满眼都是看不上的神色。
“妫龟年,你虽然贵为当朝二品大员,但你太孤陋寡闻了,你应该多读些稗官野史和奇闻轶事的书,充实自己的知识量。”
“老东西,明说!”
妫龟年有点气急败坏,早已经顾不得仁义道德了。
“莫昆昦是莫昆桑都收养的义子,他的父母是大周国朔北边民,死于战乱。他带领的那些人是‘骷髅团’组织中的精英。骷髅团组织,没听说过吧!”曹淳望那老迈的嘴角扭出一个嘲弄的微笑,“他们的祖先是大契人,他们身上流的是大契人的血,但经过几代人的更迭,他们早已经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大周国百姓,可他们骨子里做梦都想把大周国变成大契国的属国。由这样一些比大周国百姓都百姓的人组成的骷髅团,恐怕就是站在你面前,你都认不出来,除非他手持利刃要杀你。而恰恰相反,他们轻易不杀人,更不轻易露面,像蝉一般,蛰伏在大周国境内没有一点点动静,踪迹都不可寻,就像大海捞针一样。”
听得妫龟年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牢房居然跟冬天一般寒冷彻骨,顿觉胆汁涌到喉咙,就差张嘴呕出,他变得有点紧张和阴郁。
这故事也太可怕了,他简直难以怀疑其真实性。
那个时候,他还年轻,刚刚进入仕途,不太可能知道骷髅团这么绝密的消息。可眼前这个老东西,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曹淳望,你又是怎么知道这些消息的?”
很显然,声音中依旧透出一丝怀疑。
“我年轻人时在司设监当差,专门管理皇宫文书、档案什么的,记得皇帝曾经收到京都府衙密报,那上面写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段话。而且就是因为这段话,皇帝给京都府衙下了密诏,要求京都府衙以蜡烛燃尽失火为由,给慈净寺案子结案。死的是皇帝妃子,连皇帝都不追究了,关别人何事?所以,这个案子即便是有人觉得蹊跷,也没人再关注了。”
曹淳望一直朝着墙壁的嘴古怪地扭动一下,掠过他这一生中最诡异的笑,他相信距离自己仅几步之遥的那个蠢货没看见。
合情合理,说得头头是道,像是那么回事,但妫龟年觉得当时年轻气盛如日中天颇想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柴皇帝,不可能就这么算了,这与大契人骑他脖颈上拉屎有分别吗?没有?既然没有,他又怎么能忍气吞声,咽下这等耻辱?
他应该立马与大契开战,血洗耻辱才对。
一阵沉寂突然笼罩了牢房,好似暴风雨前的宁静。
曹淳望看见那个蠢货略微有点肥厚的粉红嘴唇,总是恶心人似的往上撅,知道他在思考自己说的话里面有几层水分。
“老东西,你竟然还敢欺骗我?”妫龟年用手指着曹淳望的鼻尖,尖利地吼道,“你信不信,我这就让人把你捆起来,扔进粪里,让你浑身上下爬满蛆虫?”
“哎哟,我的尚书大人,我又怎么欺骗你了?”
说着,曹淳望举起酒瓶又喝了一口酒,嘴里不断有酒气呼出,减弱了臭味。
“当今圣上有上古三皇五帝之相,雄才大略,气度恢宏,傲睨万物,气吞山河,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昂霄耸壑,又怎么会被几个毛贼吓住,草木同腐?”
妫龟年双手高举,慷慨陈词,仿若他是最了解柴皇帝的大臣。
老太监耐心快耗没了,瓶中酒已经见了底。
“妫大人,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