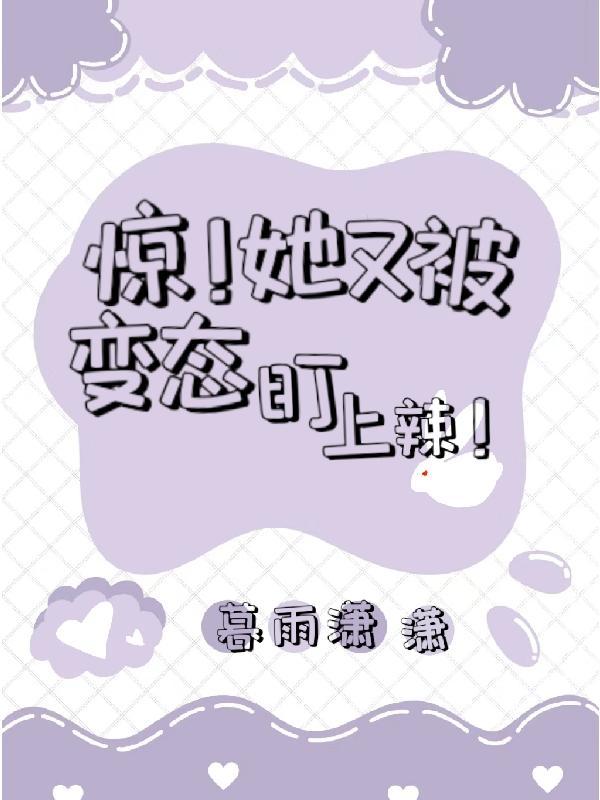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朝华令(重生)林格啾txt > 分卷阅读62(第1页)
分卷阅读62(第1页)
更不能走。”
沉沉知道她贵为谢家嫡女,坦然说出这些剖白的话,需要多少勇气,听罢,亦不由一时哑然。
只低声道“二姐”
五个月前,初入宫时,二姐还是个只知哭哭啼啼的小娘子。
如今,却什么道理都懂了。
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她说不清,可心里沉甸甸的,直往下坠。
“芳娘,不必担心我,”谢婉茹见状,用力攥紧了她的手,“你只记得,下月初一,也就是半月之后,宫中特赦的女眷经乾西门出宫,到时,各宫总管自会领了人去只是”
谢婉茹看了一眼她身后宫门,欲言又止。
“九殿下他”
宫中谁不知晓,九殿下身患疯病。
难得有人可以在朝华宫活过五个月,如今却说要把人放走。
他若起疯来,硬要把沉沉留下,谁能奈何得了他
或者说,谁又能和一个疯子计较
谢沉沉循着她目光看去,亦从一开始的欣喜若狂,渐渐地平息下来。
反而是愁惘,迷茫,还有隐约的一点不舍、丝丝点点的情绪,都渐漫上心头。
第38章离宫
谢沉沉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主殿时,魏弃正在书案前练字。
一页宣纸,密密麻麻写了大半。她看不懂,又不知怎么开口,只好先走到一旁帮忙磨墨。
阎伦留下那本古籍,此时就大喇喇地摊在一旁。
她瞟了一眼,眉头微皱,只觉写字的人实在太不讲究这都是些什么鬼画符比她写得还丑。
再一看魏弃的字,虽不认识,果然还是顺眼许多,一个个写得跟画出来似的。
“殿下,”她本就愁没话起头,当即抓紧机会溜须拍马,开口便“盛赞”道,“这、这字写得真好看不愧是殿下,做什么都是好看的。”
话落。
魏弃手中动作一顿。
眼见得墨汁在笔端晕开,沉沉忙伸手去托了一下他手腕,想把那狼毫拎开,可已经来不及,宣纸上留下个大黑团。
一副好端端的字,就这么毁在手里。
沉沉看得心痛不已,又不好说什么,只得先手脚麻利地收拾好桌上残局,把写废了的纸放到一旁,又扭头从书架上找了一张新纸,她小心翼翼把纸铺平,拿镇纸压好两头。
刚要抬头邀功,怎料,却正好与魏弃四目相对。
小姑娘到底道行浅,被那眼神看得心虚,嘴上立刻也结巴起来“写、写这张。”她说。
魏弃没动。
狼毫墨汁未干,便被随手搁在笔枕上,往书案上渗了几滴墨迹。沉沉低头去擦,避开他的目光。
忽然,却听魏弃问“她为何叫你芳娘”
这话一出。
沉沉身形僵在原地,心瞬间提到嗓子眼。
可不知怎的或许是因魏弃说完这句便不再说话,没有逼问的意思,只是等着她回答;或许是,听他的语气,既没有不耐,也没有生气。
她的心高吊起,又不知觉轻轻落下心想反正在朝华宫,什么事都瞒不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