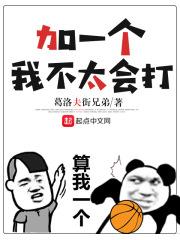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副人格消失了还会回来吗 > 第 73 章 皮影戏15(第1页)
第 73 章 皮影戏15(第1页)
好像过去了很久,又好像只是短短片刻,棺椁里一直传来闷哭的呜咽声,里面的人反反复复地说着几个字。
不停地说自己不要怀。
捂着酸软的小腹,腿根都被打湿了,眼泪不停地掉,双眼无神地睁着,看着前方喃喃重复这三个字。
反反复复,被吓傻了一般。
有人吻去他的泪。
尤黎失去所有听觉的耳中终于听到了很轻的一声叹息,“不会怀。”
但他现在能听见也什么都听不见了。
尤敛抬了抬手,抚着人的后脑,不轻不重地顺着人,“夫人莫怕,夫君说不会就不会。”
他轻声哄了许久,才见一点成效。
话是不说了,但只是着抖,蜷缩成很小的一团,于是尤敛抬了抬手,让里面的物什停了,又抚了抚人的双眼。
尤黎眼前的视线缓缓变得清晰,他看清面前人的一瞬,飞地往棺材的角落里退去,紧紧地贴着背板,很安静地蜷缩成一小团。
很警觉很仓皇地看着人。
尤敛撑起身过去,他越过去尤黎就越往角落里缩,甚至在人碰到他时,连滚带爬地往棺材里对角的角落藏过去。
像受惊的小动物。
无处可躲,却又不可放弃。
尤敛顿了顿,看了人片刻,半抬起手,“过来。”
尤黎把脸也埋进自己怀里,不停地摇头,“我不过去,不过去。”
声音里还带着微弱的哭腔,甚至底下还能看见濡湿的一片,沾着一丁点水液,些微晶亮的腿肉。
棺椁里一片沉静。
静得越久,尤黎的呼吸越是急促,他连头都不敢抬,只兀自含着哭音说,“我知道我忘记了很多事情,所以你对我做什么,我都可以尽量弥补你。”
尤敛听了片刻,“弥补?”
尤黎埋着点了下头,“我知道在我想不起来的过去,你肯定为我付出了很多,但是……”
棺椁里很大,但也改变不了任何的现状,不管尤黎再怎么躲,都阻止不了尤敛只一个动作,就能把他拽着拖过来的举措。
还是那个看不见的东西,它缠绕住尤黎,把他整个人拖着往那去。
尤黎近乎扑倒在人怀里,他说到一半的话止住,呼吸都停住,颤哭着抬脸看人。
尤敛问,“夫君说过什么?”
尤黎很想讲道理,他不敢,“夫君说……说让我过去就得过去。”
尤敛,“错了。”
尤黎摇头,很轻的,“那我不知道了。”他很努力地想进行沟通,“你说过那么多,我记不住的。”
很显然,他面前的人跟小丑和o19都不听,并不好糊弄过去。
听话和卖乖都没有用。
尤敛笑,“夫君说不用你想起来。”他抚上人的侧脸,缓声道,“过去的也不重要。”
尤黎跪坐在他怀里,仰脸看他,毫无征
兆地被轻吻住,听见人道,“想起来也好,不想起来也罢,都没什么不同。”
尤敛最后几字极轻,却听得尤黎有些背脊生寒,他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是他会一直,一直永远地留在这。
所以过去不重要了。
这就足够。
“夫人日后在此处,十年,百年,万年,记下来的会更多。”尤敛道,他看着人,也只看着人,“夫君不看近,只看远。”
“与此时、此刻。”
尤黎身上的寒意很慢地褪去了,他看着面前那张和他完全相似的脸,心底生出一股很奇怪的感觉。
面前的这个人知道他的所有过去,了解他的所有喜好,也清楚他的极限在哪。
刚刚尤黎是很难受,他蜷缩着,觉得肚子很酸,一直在抖,他从没有体验过这么奇怪的感觉,很奇怪,黏糊糊的,也很害怕。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感觉的加剧,越来越害怕。
但尤敛停手时却恰恰好地卡在尤黎的极限点,多一分,就会是适得其反。
尤黎被放开的一瞬,绝对不会是往棺材里躲,而是往棺材外跑。
现在也是,对方甚至只用一句话,就帮尤黎卸下了很沉重的负担,他眨了一下眼,有些难过。
尤黎总是会觉得自己好像欠下了所有人很多很多的东西,他不知道自己要怎么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