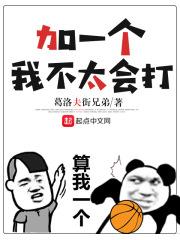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鸣女怎么变成鬼的 > 第93頁(第1页)
第93頁(第1页)
——呵呵。二十年前,老子也是這樣向你爺爺吹你母親的。
事實上,瑠火還是有不少小毛病的。比如說原生家庭帶出的內斂嚴厲,雖是美人卻很少笑,煉獄家風味的糟糕廚藝,季節性身體病弱等等,但槙壽郎就是看她好。
優點好,缺點也好,怎麼看都好,瑠火天下第一好。
咳咳,偏題了。總而言之,長子的未婚妻第一次來家裡拜訪,槙壽郎有點緊張。
長子忙著準備鬼殺隊的集訓,招待客人的準備他也不會做,千壽郎也不敢讓父親插手。槙壽郎甩手掌柜般緊張著緊張著,決定抓緊時間去喝酒——等兒媳婦正式嫁進來,大概就不能這樣肆意地喝了。
沒想到的是,及時行樂第一天,就被上門拜訪的兒媳和兒子的同事撞了個正著。
「父親,趁兄長還在做飯,你去換身衣服吧。」千壽郎趁著遞茶的間隙,低聲勸說如坐針氈、渾身不對勁的老父親,「你、你身上的……酒氣,太重啦。」
這特麼是我想的嗎?!我知道她、她今天過來嗎?!槙壽郎橫眉豎眼。
「要不然、我還是去幫忙吧?」鳴花也坐立難安。煉獄家其他貓頭鷹的廚藝她不清楚,煉獄杏壽郎的從廚房殺手等級她心知肚明——總不可能短短一兩個月,就洗筋伐髓、脫胎換骨。
老貓頭鷹愣了愣,奇怪的脾氣就上來了:「讓他做!這點小事而已!」
伊黑和千壽郎同時扶額。
小芭內:這麼多年過去了,煉獄先生怎麼還是這種性格?
千壽郎:這麼多年過去了,父親大人怎麼還是這種性格?
「鳴花小姐,」千壽郎就像這個家裡的小燕子,飛東飛西為兄長的幸福努力,「我在廚房煮了小米粥,到時候如果實在……咳,你就說自己吃飽了,我偷偷拿給你,好嗎?」
小貓頭鷹端端正正地跪坐在鳴花身邊,喏喏的語氣里透著心虛和鬱悶。
果然像阿杏說得一樣,是個好孩子。鳴花莞爾:「好,辛苦你了。」
千壽郎靦腆地笑笑。
漫長的半個時辰後,不知大貓頭鷹在廚房與廚具和食材們經歷了怎樣的殊死搏鬥,到底還是把晚飯的菜品端上了桌面——竟然勉強能看出各位菜品先生的原材料,真是進步驚人啊。
伊黑的表情已經從灰敗進化為從容。青年憐愛地撫摸摯友鏑丸,然後彬彬有禮地拿起筷子,不疾不徐向自己的人生告別:「多謝招待,我開動了。」
在座各位面前的小桌上擺著相同的菜品,分別是:能看出是米飯的米飯,能勉強看出形狀的煎魚,能看出原料的時蔬燉品,看不太出原料的味增湯,大概是什麼海鮮製成的佐飯醬……
以及三張大同小異的『人生無望,何苦來哉』臉。
鳴花心覺好笑,但這個時候要是笑出來,各種意義上都不太好。
某自告奮勇的始作俑者自知理虧,老老實實在鳴花身邊坐下,悄悄撇過來的目光不似往日般正氣凌然、理直氣壯,反而有些千壽郎式可憐。
「煎魚,不錯。」至少比我做得好,比瑠火和小兒子還差了點。槙壽郎緩慢地點評,「嗯,不錯。」
你真敢說,伊黑眼神死。他十幾歲被煉獄先生從族中救出,加入鬼殺隊前借住在煉獄家,彼時瑠火夫人病重難以起身。槙壽郎忙碌、千壽郎年幼,精神少年杏壽郎操持了一段時間伙食,水平……靠玄學。
這麼說吧,伊黑差點把自己吃死在煉獄家。
是蘿蔔湯?鳴花遲疑,又抿了一口碗裡的味增湯,篤定:是豆腐湯。
結束了痛苦而煎熬的一餐,在場的男人男孩無一人表現出再添飯的意思。伊黑馬不停蹄告別走人,迫不及待到使用敬語向眾人辭行;大家長槙壽郎則借著散步的由頭,揣上錢袋、火溜出家門。
千壽郎徹底放棄挽回家族形象,沮喪地接下清洗碗筷的工作,順便看看小米粥煮得如何。
偌大會客廳內只剩未婚夫妻兩人。門外夜色徐徐落下,皓月當空、柔光輝潔,秋初蟬鳴起伏。杏壽郎背對著紙拉門,盤腿坐在靠近走廊的位置,鳴花則含著笑意,端正地跪坐在燈下。
暖橘色的燈光將和服少女的側臉渲出一層金邊,鳴花點墨般的眼眸爍爍似皓潔月色,目光更是溫煦到令人心跳加。她光是坐在那裡,柔和平靜地微笑著,安定地注視著自己,就足夠讓煉獄杏壽郎說不出話了。
煉獄杏壽郎微笑:「……鳴花。」
少女頷回應:「煉獄先生。」
「唔姆,在家裡還是換個稱呼吧!」火焰似的青年摸摸下巴,笑著提議道,「嚴格來說,這邊可是有足足三個『煉獄先生』呢!鳴花試著叫我『杏壽郎』如何?」
「是,」鳴花從善如流地點點頭,神情溫軟,「阿杏。」
聽到這個久違的稱呼,煉獄杏壽郎頓時振奮,燈下看美人的平和熏然一掃而光。大貓頭鷹暗自估計了一下弟弟收拾碗筷要花費的時間,果斷選擇坦坦蕩蕩站起身,一本正經挪到鳴花身邊坐下。
「阿杏,」和服少女柔和地仰頭注視著他,「——你是不是,有為難的事啊?」
杏壽郎聞言一怔,半坐不坐地僵在原地。
「抱歉,其實、其實我也只是猜測,」鳴花無措地試圖解釋,「那個、雖然不太明顯,但是你今天看起來很沒精神,笑起來的時候也像有心事;煎魚、煎魚和燉菜里,有一種失落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