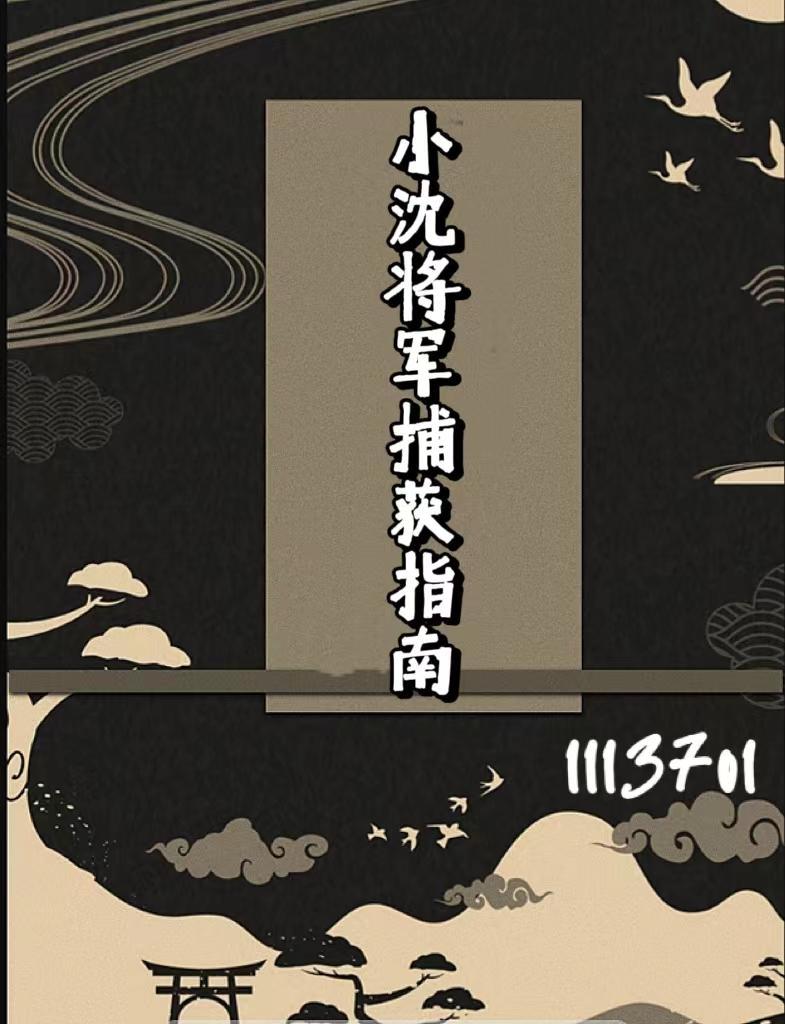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惊凉 > 回暖6出大狱各有心事(第2页)
回暖6出大狱各有心事(第2页)
谈知节又是一叹:“并非俗人——因而这朝堂阴诡之中的任何人都没有本事去利用。”
“殿下想明白了就好。”那女子舒心一笑,却明显并没有几分真情。
谈知节又哪里看不出,只是没有说破,话锋一转道:“明日眺江楼开张——眺江楼本是我出资督建,开业便是一举夺了京都第一酒楼的名头,听闻那掌厨更是自镜花水月而来……天下人多也好奇仙家吃食,自有王宫贵胄约上了宴席……鹏程巷的元家便是头一个。”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阿漱……元家与柳家的婚事本在几月前便定下。只是你远在南安的娘家弟弟跑来京都,当街骂过那元子敬。他不堪流言,这才择了期……”
那女子闻言一怔,随后叹出一口气,评价一句:“元子敬本也不是有魄力的……说来——我与他的交情并不足以他来替我鸣不平,无非是性情中人见不得糟蹋婚姻。”
谈知节知晓她后半句所指并非那元家公子,松下一口气的同时也生出些疑惑来。
半年前乱羽一只幻蝶传信,他救下被困在千金台的欧阳玉漱。
那时的欧阳玉漱虽并未像传言那般“成了痴傻”,却也再不可能回到北侯府或是元家。
谈知节手握不少北侯府把柄,私下与欧阳彰达成协议——对外宣称欧阳府嫁到元家的小女儿因病辞世,那些罪恶在太子手里便可既往不咎。
于是北侯府兴师动众办了一场丧仪,欧阳彰辞官卸甲,欧阳玉漱被悄悄养在了谈知节府中。
这位贵门小姐受了如此打击,再也不肯与曾经青梅竹马的玩伴亲近,张口闭口都是“殿下”,即便寒暄几句也保持着距离。
谈知节作为储君,历来践行“一言九鼎”,当真没再查北侯府的旧事。
他只当欧阳玉漱失望透顶丧失了对待生活的热情,如今提及元家的婚事也是希望将泥潭中的她拉出来。
眼下一看……她似乎对元子敬并无留恋。
谈知节正不知该说什么,又听欧阳玉漱开了口。
“难为了柳家姑娘,清清白白,却要给人做续弦。”
谈知节心中一紧:“阿漱……”
“殿下,半年前欧阳府已办过丧仪,欧阳玉漱早是泉下人。这称呼若被旁人听了去,只怕要说殿下疯魔了。”
谈知节意外她能说出这样的话,一时间生出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他正思索着该说些什么才好,却听外头传来敲门声。
谈知节并未许人进门,提高了音量问一句:“何事?”
来人轻声接话:“殿下,凌小世子求见。”
谈知节不禁疑惑,自语一般道:“都这个时辰了……”
他略一思索,回了外头的家丁:“将人请去正厅,本王随后便到。”
与此同时,城南的眺江楼里,盼星星盼月亮的几人终于等回了乱羽。
在那牢狱之中待了几日,这平日里最为恣意的齐少侠眼下也是恹恹的样子。
他面上可见几道浅浅的鞭痕,并不渗血却也有些红肿。早是凌乱的,让人打眼一瞧便知晓此人经了磋磨。只是不知为何,他进了屋也不肯解那大氅,手里似乎还拽得更紧了些。
李英琦终于见了他,年近不惑的人了还隐忍着泪花。
“臭小子,终于舍得出来了?”
他颇为怨怼地白了外甥一眼,嘴硬道,“你既平安出来了,我便安心回去——这几日天气寒,客饮居客人来了不少,没了我——好些生意可做不了。”
乱羽哪里不明白他是想留他们几个同龄人自在叙旧,抱歉地低了低头:“让舅舅担心了。”
李英琦走后,刘子诺看了看余下几人,搓搓手道:“几位,我这眺江楼明日开业,要忙的事可不比今日少——我也回去歇着了,几位自便?”
唐星翼点了点头做了代表应下,与宋灵雪交换了一个眼神,又看向乱羽,道:“在那狱中滋味可还好受?药箱已经备下了,随我换药。”
几乎是他话音刚落,宋灵雪也拉过了洛笙:“舒颜,你今日才来,尚未寻到落脚的地方吧?先随我去旁边的客栈歇着。”
洛笙闻言,下意识看一眼乱羽,见他并没有要开口的意思,这便应下,随着宋灵雪出了门。
唐星翼则将乱羽带到了楼上一间杂物房,随意搬了张凳,指了指让人坐下。
乱羽舒下一口气,终于解开了身上的大氅。
![今日放晴[先婚后爱]](/img/22774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