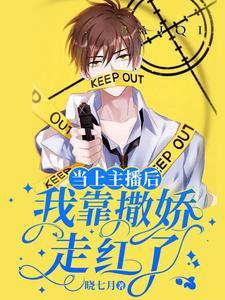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吞噬鳗视频 > 第32页(第2页)
第32页(第2页)
“尼莫!”她高兴地叫道,“我把它绑在你的床头上好吗?”
我舌头僵硬,几乎不能说话,我呆呆地看着那条橡胶玩具鱼,觉得那张裂开的嘴仿佛是在从我大笑,带着一种无法掩盖的恶意。
“怎么了,爸爸?”莎拉的小脸垮下来,“你不喜欢吗?”
“不,不。”我回过神,“我很喜欢,宝贝儿……来吧,来把它绑上去。”
莎拉重新变得高兴起来,她把那条小丑鱼绑在了我的病床床头。
我笑着伸手拨弄了它一下,闭上眼睛。
索菲抚摸着我的头发,用担忧的语气问道:“怎么了,马修,哪里不舒服吗?”
“我只是累了,”我拍拍她的手,“我想大概是因为肚子太饿,还有我刚刚才醒过来。”
“嗯,那么,你再好好休息一下,我去跟医生谈谈。走吧,”她对莎拉说,“我们让爸爸睡一会儿。”
莎拉依依不舍地看着我:“你会很快回家吗?”
“当然。我很快就会出院,回去,和你们在一起。”我看着她的眼睛向她保证,那是漂亮的蓝眼睛,跟莎拉的绿眼睛不一样,跟我的黑色眸子也不一样。
莎拉露出灿烂的笑容,牵着她妈妈的手,一蹦一跳地出了病房。
我凝视着她们的身影消失在外面的走廊里,回头看着天花板——
我想我的确是明白了一些事情:我自从十天前醒过来,就陷入了一个圈套。我的模样被改变了,我的生活完美无缺,漂亮的妻子、听话的女儿;失去的朋友重新活了过来,围绕在我周围,生活得美满、幸福;有些不好的秘密被封存起来,没有人再知道——如果被揭开,也很快被擦去……
绿湖镇安静、祥和,气候宜人,到处都没有纷争,我们和所有的人相处愉快。这里几乎就是天堂。
当然,也只是几乎。
我心中有些可怕的猜想,我能猜到谁能做这样的事,但我由衷地希望这次是我错了。
我拔掉了手背上的输液针头,从床上坐起来——还好因为我醒来了,那些监视闹电报和心跳的线已经被拆了。我悄悄地下地,感觉左脚有些刺痛,大概这就是从枪击变成扭伤的效果。我试着踩了两步,还能走,也能用力。这实在是太棒了。
我穿上黄色的绒布大衣,从病房里拿出备用的拐杖,装作一个最不起眼的病人,从电梯下到底楼,然后寻找着停车场中的机会。
终于,我在一个角落中发现了一辆破旧的尼桑轿车,它孤零零地停在那里,被几辆高大的货车遮挡住了,上面落满了灰,也许是某个住院病人的。
我看了看周围,确定没有人,然后用手肘打破车窗玻璃,开了门,坐进去,用卑劣的少年时期学会的偷车伎俩发动了它。
我溜出医院,一直向绿湖开去。
那把钥匙,就是挂牌上写着“ff”的钥匙,其实并不是属于城里的某个低档酒吧的储物柜。我想我从梦中得到了真正的答案——
那是属于绿湖的钥匙,我得去那里寻找它指向的东西。
我把车开到了绿湖周边,停在一个隐秘的草丛里。
这车的主人大概年纪不小了,在车中放在一些急救的东西,还有手电筒、饼干和水一类的。我毫不客气地把它们都带上,然后下了车。
乔治?洛克伍德在绿湖里游泳,他才是这一切的钥匙,我知道那个梦告诉我的是:答案在绿湖。
我沿着湖边跌跌撞撞地寻找着,避开那些经常有人的景区和适宜于野餐的平坦空地,走入了绿湖边缘很少有人来的区域。这时候接近黄昏,眼前的景色与我们过去游玩过的绿湖完全是两个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