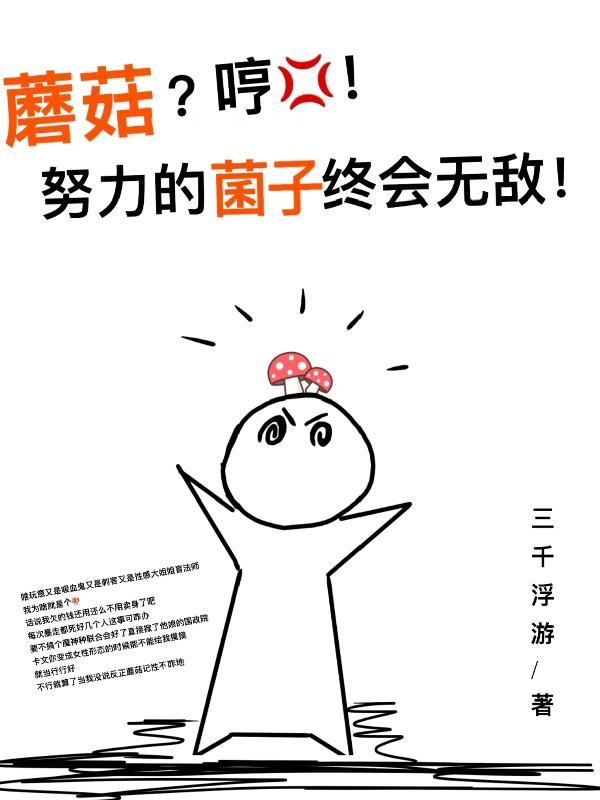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从龙王传说到大神圈的 > 28收局(第2页)
28收局(第2页)
云行之恨道“你利用我”
泓道“不错,确实利用了你,都过去这么久,不要生气了。”
云行之见泓云淡风轻不当回事,登时气疯,挥拳直出,把泓打得偏过了脸。这一拳实在是有点疼,泓也不高兴了,反手扭过云行之的手腕,怒道“你不是也在利用我吗互相用一下,干什么这么生气”
云行之被他扭得肩膀生疼,使劲挣了几下,大吼“我没有”
泓放了手,提防着他再打过来,退了半步说“你要我帮你在陛下面前美言,又要我探陛下口风,我都做了,也没有像你这样生气。”
云行之莫名觉得冤枉,大吼“我才没有”
泓反问“没有和我刻意结交吗也没有在我这里探消息吗”
他不过是随口一说,到后来却想起差点被云白临下毒,害陛下担忧的事来,语调便越来越冷,静静问“当初结交,不就是为了各取所需,互相利用吗你我均从中获利,交易得好好的,处得也还融洽,为什么要生气因为你拉拢了我,我却没肝胆相照,认你是个知己吗”
他的话仿似一盆冷水,兜头浇得云行之熄了大半怒火,怔怔地说不出话来。
是了,一开始和小哥结交,就是看上他是个天子近臣。
所以才投其所好,使出了圆滑手段拉拢逢迎,想拉他上船,将来为自己所用
。
拿出剔透心思,揣摩他的喜恶,掐着松紧,和他培养深厚情意。小哥生性内敛疏淡,他软硬兼施,花了多少玲珑心思,下了多少水磨功夫,用了多少细致手段啊
才换来今日这场真伤心。
他素来有伶俐七窍,圆融手段,人情宴里八面敷衍,名利场上四方参透,但凡有心结交,哪个不和他好得蜜里调油既然盯住了一人下功夫,水滴石穿天长日久,自然是拉拢得亲密无间无话不谈,自觉两人已经情深意重,肝胆相照。想不到小哥始终清明,他反把自己笼络了进去
云行之又气又恨,满腔愤怒委屈却又无言以对,只得狠狠瞪了泓一眼,扭过了头。
泓也觉得自己说得过分了,便放软了语气,道“别生气。你我立场不同,迟早有冲突的时候。但我是当你这个朋友的。”
云行之恨恨道“你要真当我是朋友,就不该威胁我家族”
泓静静道“我是武者。不为私情妨碍大义,是我的职分。交情归交情,我既然侍君,就应该和你家划清界限,以免勾连不清。这是给你父亲的警告,他再有妄动,我出手不会容情。”
他说完顿了顿,见云行之一脸崩溃,就轻声道“你我各有立场,是为大义。但你若有事,我不会旁观。放心,我会保护你。”
他素来沉稳内敛,若不是放得极重,绝不会轻易许诺。云行之早摸透了他的脾气,听他一说,心气才稍稍平和,勉强满意。转念一想又不放心,低声开导“天下臣子,都是一个立场。你做不做纯臣,和站在哪里无关,要看那位怎么想。说你是,你党羽遍天下也是;说你不是,你就算大义灭了亲也不行。你一生悬命,全拿来侍君,可须知花无百日红,现在不留退路,以后可怎么办呢”
泓见他真心为自己担忧,便微微笑了,轻声道“不用担心我。我没有畏惧。”
他们两个捅开了窗户纸,这时候反倒更好说话,云行之便和泓互叙别后诸事,他知道泓有个老父亲在无赫殿,往日也曾时时问候,这时候便问他安康。
泓替父亲谢过,答“现下不在宫里,正外头办差。”
泓的父亲身份颇高,早已不用再接外差。
云行之出乎意料,怔了怔问“老人家还没歇下来”
泓笑一笑,答“偶尔还是会接点差事,顺便活动活动。”
无赫殿最讲齿序,寻常外差都派低阶武者去,也有历练的意思在里头,若不是大事,断不会让侍剑人接手。云行之心中一动,不动声色地旁敲侧击,道“快入冬了,鸟兽都肥。什么时候方便,咱们再去后山围猎。”
泓说“现在宫里无人,大家都在外面。等你下次回来,我叫上人好好闹一场。”
云行之垂下眼睛,心内一阵狂跳。
半年前入宫,小哥就说过御前影卫都奉了秘旨在外面办差。到底是什么样的大事,一办办了将近一年,需要无赫殿自上而下,倾殿而出
今年就这么一件大事眼下还没完。
所以无赫殿的众武者,也还在外面。
云行之再也坐不住,敷衍了几句和泓相约日后再聚,拔腿回家就把此事告诉了祖父。他在这方面是极敏锐的,云安平从不轻忽,当即叫人前去打探。没几天传回消息,隐隐约约也不是很确定,说这次五州中,似乎见着了几位武者。凡事若有了个方向,只需抓着尾巴严查就是,云安平忙派了大批斥候过去,详查那十几万役夫和五州众民中带头挑事的领导者背景。
斥候们浑水摸鱼,连查十几天,却没现丝毫异状。十几万人一朝起事,湘邦五州遥相呼应,全国民怨皆沸,这里头多少投机,多少煽动,多少利益纠葛,又有多少趁火打劫,怎么可能一点异状都没有没有异状就是最大的异状,云安平一颗心沉到谷底,和云白临密谋半日,换了个方向探查,派心腹武者亲去湘邦州府,直接清点当地守军人数。
这一次果然查出了端倪,消息很快传回来,道湘邦某州有两名千夫长不在任。地方州府守军都是系将的,即所谓兵随将走,两名千夫长不在,意味着麾下兵将全带走了,他们秘密探查了三个州府,现皆有千夫长旷任。消息迅送到云府,云安平和云白临相顾骇然,一时间面面相对,说不出话来。
漓江沿岸,加上湘邦五州,到底少了多少兵那无赫殿上上下下,在役武者数百人,又全部外派到哪里,,,请牢记收藏,&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