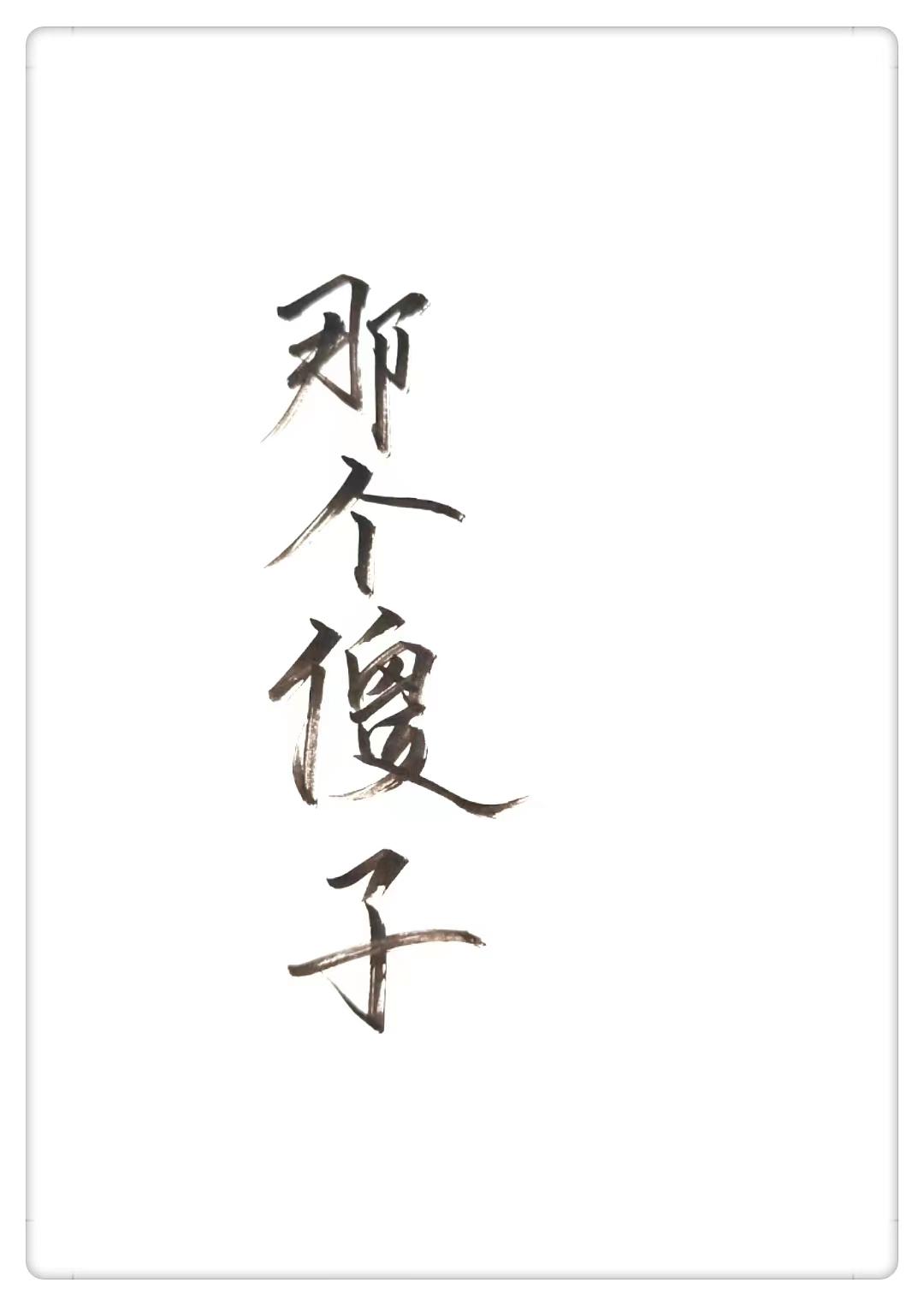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血色黄昏 > 第四十五章 恶寒(第2页)
第四十五章 恶寒(第2页)
“你们两个别那样了,快给人家道歉。”说罢,那个年轻女性走到唐烟樊身前,“唐小姐你好,我为我们刚才的莽撞表示抱歉,我的名字是沈云,希望今后多多关照……呃不是,我是说……”她说着说着皱起了眉头,脑内是组织杂乱的语言,由于饥饿,她无法做出准确判断哪句该说哪句不该说,就这么停了下来自顾自犯起了难。
“哪个……你是饿了对吧,刚刚还说三天没吃东西了来着……我包里有几个夹心巧克力棒,你们……”说着,唐烟樊翻起了腰间的小包,从中拿出几条夹心巧克力棒和一瓶矿泉水来,展示在沈云面前。
“啊……感激不尽!太谢谢你了……”沈云一边谢着一边接过了对方手中的巧克力棒,剥开了包装,小心翼翼地咬了上去。
“喝点水别噎着了……你们也过来吃点吧,我包里还有挺多的。”
……
在分享了食物和底细后几人的关系和缓了起来,围在煤油灯旁一起小声地闲聊着些有的没的。
“所以原来你也不知道啊。”那个领头的男人说话了,他叫孟子翰,高中辍学后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打拼,似乎生了很多事,但看得出来都已经过去了,他现在最烦恼的是还没干出什么大事就奔三了。
“这么说起来,我还知道和你的事情并列为天元市五大诡异事件的几个,我说来你听听,我想知道本地人听没听过……”说话的是那个眼睛男,他叫黄覃,去年刚来这座城市,对一些神神叨叨的东西很感兴趣,曾因创业失利差点轻生,但目前对自己的工作十分满意——如果没生这种事的话。
“都跟你讲了,网上传得太夸张了……”这是沈云,本地人,是通过网络认识的其他几人,在几人的小团队里风评不错,现在担任的也是主播的位置,现在因为胆小而想要换工作,但正是因为她胆小,有个风吹草动反应就很大,并且还能以极高的语往最恐怖的方向说出自己的揣测,才让直播更有节目效果。
“总而言之我听听她们两个怎么看吧,咳咳……传说,在五年前啊,那天元大厦附近生了一件怪事。”
“五年前的话我还没出院。”唐烟樊迅说道。
“啊……咳咳,总而言之,咳咳,有辆小轿车,往人行道上横冲直撞,据说撞死了十多个人,还有很多人受伤了,警察赶到的时候怎么喊都拦不下来,终于用那个就是丢地上扎车胎的玩意强行拦下来后却现一件事——那辆车上根本没有人,调监控也看不到一个人。”
“没听过。”
“没听过吗?”
“真的没听过。”
“那好,下一个,咳咳,从前年开始啊,有人注意到一件事。是什么事呢,有个穿着黑色风衣的男子频繁出现在那些难以解释的案件现场,比如血斧案啊,古剑案啊,这些你们总听说过了吧,总而言之,有人现现场的照片中总会有那个黑色的背影,甚至之后出现了更为诡异的事情,在人们开始注意后有人现,他在一些案件生之前就已经出现在了现场附近,甚至和受害者有过接触,而这些人在和他接触后不久就会死去,就像收到了什么死亡诅咒一样。但是即使被目击多次,他的脸还是都没有人能拍摄清楚,就像是被什么自然力量干扰了一样,他的脸永远是糊的。直到现在都没有人搞清楚他到底是谁,和案件有什么关系,他的存在就像一个死神一样——有人猜测,他就是黑白无常的化身,一旦出现就宣告了某人的死亡。”
“这个我倒是听说过……你呢?”余琴看向了一旁的唐烟樊。
却现唐烟樊此时笑得十分不自然,脸上时不时冒出些心虚的冷汗。
没错,这事唐烟樊当然听说过,她也知道——她可太知道了。
什么出现在许多案件现场穿着黑色风衣的诡异男子,那不就是罗牧吗?
一定要找一堆拍到罗牧的现场照片然后说罗牧是什么黑白无常啊那不就是先射箭后话靶吗?
甚至举例的那俩案子的现场照也拍到唐烟樊了,但是由于两张照片衣服不同所以没人看出来。
“我前年出院的没错……但是……咳咳,我,我没听说过这种事。”
“那可能是你信息不怎么灵通吧,好,我继续说啊,这是三十年前的故事啊,据说天元大厦建成后,有层楼啊一直……”
“你记混了吧?”沈云轻轻拉了一下黄覃。
“啊……我想想啊……”
“想不出就别乱说啊。”
“好好好听你的,你们本地人知道什么吗?”
“这个我知道挺多的,比如那个血斧案啊……”余琴表情有些兴奋。
“告诉你们,那个其实啊,就在我家附近……虽然这里也在我家附近就是的了。”
唐烟樊坐在地上端着下巴,稍微低着头盯着煤油灯,眨了眨眼。
血斧案啊……那是她进事务所后办的第一个案子。
据说因为那个案子让是罗牧实在一筹莫展才想起精神病院有个人能帮他,就这么着唐烟樊才从精神病院出来。
记得那个犯人手持一把上面有许多斑点不知是凝固的血液还是锈迹的斧头连续砍伤数十人,而罗牧的把戏完全无法正面对抗,但想要击败他却恰恰需要正面去战胜对方。
虽然战胜得很轻松,但那个案子最麻烦的是后续。
被砍伤的人伤好后都表现出了明显暴力倾向,仿佛是被传染了什么戾气——其中一人更是据说回家看到自己的妻子和别的男人在沙上搞在一起而自己的女儿就坐在一旁看电视气得怒火中烧提刀将三人砍至重伤,其中两人没有及时送医而导致失血过多身亡,只有女儿被勉强救了回来——而这次后续是经过亲子鉴定现连女儿都不是他的而是妻子出轨对象的气得急血攻心就这么一命呜呼了。
至于为什么她记得这么清楚——她当时就在附近,被罗牧派来监视。
“啊,然后啊,那把被诅咒的斧头现在就在市博物馆,不知何时还会有人再去盗取,然后引下一场闹剧。”
“啊……说实话你讲得不恐怖,但是挺有意思的,像在听故事……不对本来就是在听故事。”黄覃对余琴笑道。
“那我也再讲一个,那也是五年前的故事啊……”
这次闲聊聊着聊着就变成了故事会,一群人围在一起分享自己知道的怪谈故事,但只有唐烟樊始终没讲。
而是一直在回忆着。
因为他们讲得大多数故事自己都见证过。
很快,他们都感受到了倦意,一看时间也已经入夜,但并非没有地方去睡——杂物间角落放着三卷地毯,刚好可以作为睡觉的毛毯和被子。
最终是这样分配的,黄覃和孟子翰共用一张,唐烟樊与余琴共用一张,剩下一张稍小的由沈云独自使用。
唐烟樊和余琴裹着地毯靠坐在墙边有些尴尬的沉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