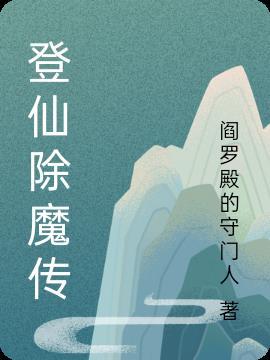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欠佳的意思是 > 第37頁(第2页)
第37頁(第2页)
「賀祺,你非要這麼對我嗎?」
賀祺怔了一下,不明白蔣洛盟具體是在指什麼,但心中卻已經有了些幽暗模糊的預感。捉不住具體的詞句,卻已然讓自己的心跳又快起來。
蔣洛盟的胸口起伏了一下,接著開口,語氣中的強硬與堅定不減絲毫:
「就因為我知道你喜歡男人,所以你就要像避瘟神一樣避著我?你能不能不要這麼針對我?」
「什,什麼?」賀祺瞪大了眼睛,緊張到下意識結巴起來:「誰說……誰喜歡男人?!」
蔣洛盟不再說話了,只是看著賀祺沉默著。
儘管樹底昏暗,賀祺還是很真切地看到了蔣洛盟的眼神。
那不是拿不出證據時心虛的沉默,而是根本不需要證據的堅信、認為爭辯沒有必要的沉默。
蔣洛盟的胸口平穩地起伏著,黑曜石般的瞳孔定定望向賀祺的眼睛。
賀祺全身都在細小地顫慄,也許是因為濕衣服在身上貼了太久,讓亞熱帶長夏的雨夜也冷了起來。賀祺完全能想像到,此時開口,他的聲音會多麼虛飄顫抖,說出來的字句會多麼蒼白而可疑。
賀祺沒有辦法,震驚與懼意交織,他的目光開始不定地閃爍起來。
賀祺知道此時言多必失,便也強作鎮定地沉默。可賀祺的沉默與蔣洛盟的不同,更像是無可奈何的默認。
蔣洛盟閉了閉眼睛,語氣軟了些:「我知道,這件事你不希望別人知道,我不會告訴任何人的。」
賀祺藉機逃脫了蔣洛盟的注視,輕輕垂下眼神,乾巴巴地說:
「這只是你的猜測,我並沒有承認過。」
但也並沒有否認。
「呵……」蔣洛盟也低了頭,有些沉悶地低笑了一聲;抬起頭時,眼神昏暗而複雜,聲音更輕:
「好,那我這樣說——
「如果你願意試著交男朋友的話,我會很高興的。」
此時賀祺也忍不住出聲笑了,但更接近於苦笑。
是入世者對天真者的嘲諷,是對蔣洛盟盲目的理想主義的哂笑。是自己的磨難被想當然低估時的心寒,想要用笑來稍顯得體地掩蓋,卻拙劣至極。
「為什麼?」
賀祺心口仿佛壓著塊冰冷沉重的石頭,朝蔣洛盟瞪著眼睛:
「是因為你覺得,只有交了男朋友,我才算是終於在嘗試『做自己』了?」
蔣洛盟卻即刻搖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