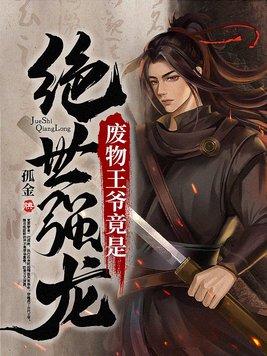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白天也想你七千折戏 > 第六十六章 密王暴毙(第1页)
第六十六章 密王暴毙(第1页)
圣旨传下去半个来月,启元的身体倒是当真越发的不好了。
按元隽的说法,在召子侄入京的圣旨传下来之后,他便已派人传信告诉了宫中的赵婕妤,可停止对皇帝下幽魇香了,以免长久之下再生变数。赵婕妤那里也已照办,但显然,心魔一旦被勾起,便没那么容易消退了。
这日元隽自宫中侍疾回府时,脸上布满了清晰可见的阴霾。裴筠筠在门房等回他来,一路跟着他回到寝殿,他愣是一句话没说。
遣退了殿中侍女,她在一旁默默看了他许久,也不急着说话,径自铺了案,摆上了茶具。
她取了年初的雪水、明前的龙井,徐徐为他泡了一壶茶。一举一动,皆是矜贵娴熟,而元隽亦在她的动作里,找到了一种罕有的……归属感。
忽然,他说:“今日在宫中,他在迷蒙之间,有几句梦呓。”
裴筠筠心头一动,没有问,只是安静的看着他。
又过了许久,元隽告诉她,启元说的是,兄长,别杀我,我错了。
事情就是这样,即便你心中已经认定了真相就该如此,可千般确凿铁证摆在眼前,都不及当事人亲口承认这一句来得震撼人心。
她想象不到元隽当时的感觉——即便对于这位皇叔,他本该是早已无所期待的人。
至于元隽,他则在出宫回府的一路上都在想,幸亏,自己听到这句话时,身边没有旁人。
“你……究竟有没有想过,启元身
后之事?”
听到裴筠筠这样问时,他的第一反应却是觉得好笑。
记得早前长姐小产出事时,自己心绪阴沉,她那时便说过,她是个不善于宽慰人的。而之前看她摆案煮茶,倒是很得他心意,一时之间,竟叫他忘了她本色如何。
好在冷静这么长时间,他也够了。如今长出一口气,浅抿了口茶,他不答只问:“你说呢?”
要她说,他自然是想过的。
其实这会儿想起来,她发现自己这个问题问得却是不对。她应该直接问元隽,是不是直到这会儿,他心中的继位人选,仍然是元殊不变。
可看元隽这样的表现,多少也算给了她一个答案。
裴筠筠沉思许久,蹙眉道:“难道即便是如今这样的情况,即便你已能认定他弑兄夺位,你也愿意让他的后人来掌这本该属于先王的江山吗?”
对此,元隽沉默许久,答案唯有一句话——“元殊,不是启元。”
他话音落地,裴筠筠一下子站起身来,无比烦躁的在原地绕着圈子。
她不是不能理解他与元殊的兄弟情——甚至于,她还觉得这情分很可贵。但是,于私,她做不到宽容大度的让启元之子坐掌江山,于公,她也不觉得元殊有本事保江山安定,大齐不灭。
元隽安静的看了她一会儿,忽然开了口。
“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没问你。”他眼里带了点疑惑,隐隐透着稚子般不设防的天真,“你的真实身
份,眼下看来,定是与前朝皇室息息相关的。”
“是。”
她这样干脆利落的回答,倒让他颇有些意外。
过了会儿,他问:“那你觉得,这个皇位,是该姓元,还是应该姓嬴?”
她瞳孔微微一缩。
两人对视之间,并没有火药味,可那根弦却绷得很紧。
裴筠筠不知在想什么,等她打算好要开口说话时,外头却突然传来了开门声,一转眼,叶檄便一脸焦急之色进到了殿内。
“……殿下!”他抱拳道:“属下唐突,殿下恕罪。”
元隽见他这副模样,便知不好,直接问道:“出什么事了?”
叶檄道:“眼线来报,说是密王在来京路上出事了!”
元隽眉峰一皱。
羽雁的眼线传回了消息还只说是密王途中着了道,中毒不起,不知情况如何。而等密王府的亲随八百里加急入宫觐见时,带来的则就成了密王殿下的死讯。
一时间,密王暴毙之事震惊朝野,自天都往外,传得沸沸扬扬。
这日元隽方从宫中回来,裴筠筠问了几句朝中局势,便好奇起来:“素闻密王身边高手如云,一流刺客,三五成群都近不了身,怎么这么轻易便叫人将命给夺去了?”
“都说是着道中毒,自然谈不上刺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