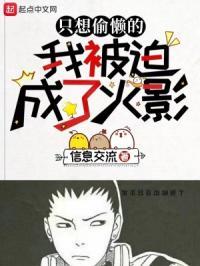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午夜杀生大招 > 第2章 本能反应(第4页)
第2章 本能反应(第4页)
确切地说,他被那满口的肉香俘虏了。
那年月,即使过年,也没有几个人能吃到这么香的饭菜。
他嘴里嚼着馒头肉,举起酒杯,“咕咚”喝干了一杯酒,再夹上一口菜,连吃带喝起来。
“你练过功夫吧。”黄墨轩问。
“是啊。”彪子对吃的兴趣,远远过回答黄墨轩的问题。
“还摆弄过枪。”黄墨轩又问。
“是呀。”彪子愣了一下,这是警察局,他这话说的太直白了。
转念又想,已就这样了,大不了再被送西山去,先解馋再说吧。
彪子又掰下一只鸡大腿,还是冲黄墨轩谦让一下,黄墨轩摆手拒绝,他把鸡腿塞进自己的嘴里。
“你在哪练的这身功夫。”黄墨轩对彪子身世的探究,远远过这桌酒菜的诱惑。
“俺姥爷活着时,教俺用香火头练的。”彪子这张倒霉的嘴,一不留神,还是说出了大实话。
啥都别说了,黄墨轩一听就明白了,这小子的姥爷肯定是土匪。
黄墨轩早就听说过,土匪练枪法,通常都是关上灯,瞄香火头,久而久之练出了百百中的功夫。
彪子在警察局长办公室,大口吃着烧鸡和肘子,满足了黄墨轩的好奇心。
在古城街头,十几个长枪警察,坐上一辆大卡车,来到市立医院。
他们奉黄墨轩的命令,把市中心街头的两个死倒拉上,送到市立医院太平房,还得留下两个警察,为这俩死倒站岗放哨。
卡车开走了,这两个警察目光相对,不约而同把视线转向医院大门口的打更房。
大冷的天,傻逼才肯老老实实守在太平房门口,为两个死倒站岗呐。
两人缩脖端腔,一溜小跑,敲开打更房门,脱掉大衣,围着火炉取暖。
警察离开太平房时间不长,寂静的夜空中,传来了清脆的马蹄声响。
一辆带棚马车,不紧不慢走进市立医院大门,直接把马车赶到太平房门口。
车老板穿了一件羊皮大衣,戴了一顶狗皮帽子,脖子脸上还围了一个大围脖。
他把鞭子插在车辕上,跳下马车,晃着膀子走到太平房门前,“咔吧”一声,掰断了门锁,就要往里进。
在打更房烤火的警察,及时现了这辆马车。
一个警察眼瞅着车老板徒手掰开了门锁,他推开房门,一声吆喝道:“住手,你是干啥的!”
他说着,挥舞手里的长枪,向太平房跑来。
车老板瞥了警察一眼,径直走进太平房。
另一个警察也跟着跑了出来。
两人一前一后,边跑边拉动枪栓,子弹上膛。
车老板从太平房里扛出一具尸体。他把尸体放在马车上,静静地等候两个警察来到近前。
这是什么人呀。
眼瞅着警察举枪跑过来了,他还不慌不忙的扛了一具尸体出来,而且,还没有跑的意思,老实儿地等在那,简直没把警察当盘菜。
两个警察似乎知道了这个人的身份,他俩很紧张,但更气愤。
他们仰仗手里有枪,而且还子弹上膛了,必须要在形式上,给这个目中无人的家伙上一课。
两人跑到太平房门口,“呼哧、呼哧”喘息着,不容分说,就把枪口对准车老板了。
车老板子表面无动于衷,其实早就做好了防范准备。
他在两个警察还没站稳时,就踢腿挥臂打出一套组合拳,把两个警察打倒了。
“啪”地一声枪响。
一个警察手指搭在扳机上,临被放倒前扣动了扳机。车老板躲闪一下,子弹从他的肩上划过,把羊皮大衣穿了一个窟窿。
“我操!”车老板急了。
他抬脚便踢警察的脑袋,一脚不解气,再来一脚,这个警察“嗝儿喽”一声,那世去了。
另一个警察摔在地上,知道大事不好了,他慌忙举起枪,就要开火。
车老板猛地来个旱地拔葱,他原地跳起,将膝盖对准这个警察的哽嗓咽喉,瞬间身体重重落下去,只听“嘎巴”一声,警察的脖子断了。
也就是几秒的时间,车老板干净利落,杀了两个警察。
他也顾不得装稳重了,知道这事一旦被人现,那就是个大麻烦。
他跳上马车,拔下鞭子,当空一甩,“啪”地一声,辕马四蹄蹬开,一路飞奔而去。
说来也巧,郑涛受伤就住在市立医院二楼,离太平房直线距离不到五十米。
他被枪声惊醒,职业习惯,起身要查看动向。隔窗看见,一辆马车飞一样跑向大门。
他借灯光看清了赶车人的装束,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多嘴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