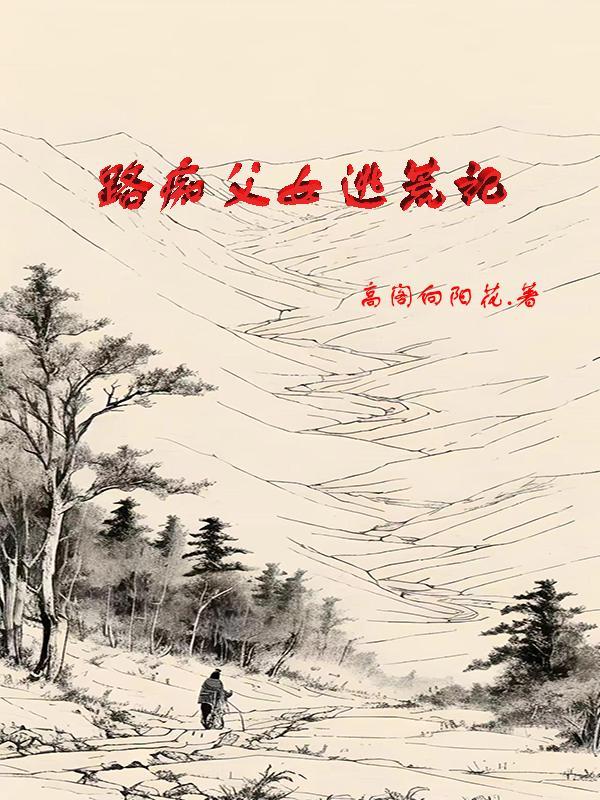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中师生名录查询入口2023 > 第107章 不是那块料(第2页)
第107章 不是那块料(第2页)
“生产一切正常,工人没一人请假旷工。就是有点不太好管,一说她们就嬉皮笑脸。”曹盛世老老实实地说。
“那是肯定的。几十个年轻姑娘,就你们两个年轻小伙子,你俩就是大熊猫。莫说管不听她们,她们没把你两个生吃就不错了。”赵厂长说。
“曹老师是她们的偶像,有几个女工喜欢他。”甄克凌看戏不怕台高地说,曹盛世拦都拦不住。
赵厂长说:“曹老师看中哪个就给我说,等两天我来给你们牵线。甄老师呢,你的销售跑得怎么样?”
甄克凌说:“舅舅答应年底帮忙销几百双。我在柳树坪乡烟草站有个兄弟,也答应帮忙找区烟草站和柳树坪乡政府销一百双。然后就打算去找商场和小卖部推销。”
“呃,不对呀。区皮鞋厂刚开始生产,区长就给区烟草站站长打过招呼,每年要在厂里买一百双皮鞋。你那个兄弟叫么名字?未必有那大的神通要他们站长还买一百双?”赵厂长皱眉道。
甄克凌心里虚,说:“厂长,我那兄弟人人都叫他鹏哥,在社会上很吃得开。他答应得很爽快,照说不会是假的吧。”
“他呀?一个好谎谎!工作不认真搞,只晓得赌博。他现在只怕尾巴尖尖上都欠的赌债。我爸现在硬是不准他进我家的门了。”姬会计鄙夷地说。她口中的谎谎是兴元县土话,形容胆大什么事都敢做的人。
姬会计一番话,惊出甄克凌一身冷汗。
鹏哥是姬会计的远房表哥,初中毕业后回村当了农民。五年前,姬会计爸爸想办法活动县烟草公司经理,把鹏哥招成合同工当乡烟草站收购员。鹏哥只在乡烟草站收完一季烟,就染上赌博恶习。输光了工资就借钱赌,估计现在欠赌都好几万了。
但鹏哥这人混社会很有一套。他为人特大方,和朋友在下馆子他总是提前把钱付了,同事家有红白喜事他总是随礼最多的那个人。他很会包装自己,即使身无分文,但仍脸不变色心不跳地示人以大款形象。
鹏哥还有个本事,区烟草站、柳树坪乡政府不管谁当一把手,他总能把他们哄高兴最终成为铁哥们。正因如此,人人都尊称他鹏哥,以和他交朋友为荣。
知道鹏哥欠赌债的并不多,因为鹏哥从不随便找人借钱。他借的都是烟贩子的钱。每每赌输了钱,他就找烟贩子借万儿八千,说和烟贩子联手做烟生意赚了钱再还钱。
烟贩子巴不得有烟叶收购员和他们成为一伙,鹏哥借钱有求必应,却从不见鹏哥还钱。有几个烟贩子实在受不了,转弯抹角找到姬会计爸爸,请他老人家帮忙做工作,家里人才晓得他已浑身是债难得翻身了。
甄克凌说:“我幸亏给赵厂长汇报得早,稍晚两天将一百双皮鞋交给了鹏哥,那就亏大了。”
赵厂长说:“社会就有这么复杂。这件事也给我们厂敲响了警钟,推销产品搞得不好就可能上当。往后去跑销售,因为都是先货,再收款。一定要把人看准,可能赖账的绝对不和他做生意。我今天就宣布一条,谁销出去的谁负责回收货款,收不回来就扣工资。工资不够还货款,就从自已家里拿出钱来填窟窿。”
甄克凌明白,赵厂长虽没把话说透,其实就是在变相批评自己。他一肚子委屈不敢表露出来,就心不在焉地听赵厂长说了半天,脑海里两个不同的鹏哥交相出现。
甄克凌不相信自己做不好销售员,他终于肯放下所谓的面子,去县城的小卖部、商场上门推销区皮鞋厂生产的皮鞋。
尽管他觉得自己像个乞丐,使出了浑身力气,在每个小卖部都低声下气介绍产品,跑了一个多月,到头来还是没说服一家小卖部,愿意从区皮鞋厂进货销售。
他去第一个小卖部推销皮鞋,店主开始用警惕的眼神看他摆弄皮鞋,半信半疑地听他讲皮鞋的质量如何如何好,直到他说自己是老师出来打工当推销员,店主脸色才稍好一些。
甄克凌说他的皮鞋质量好,出厂价格便宜,希望老板从他们厂里进货。店主见他可怜,对他说了真话。他在省城小商品市场进同样的货只有十块钱,照样可以卖三十块,为什么要进二十五块钱一双的鞋子来卖?
他回厂里建议赵厂长,把销售给小卖部和商场的价格调低些。
赵厂长却说核算过成本,一双鞋必须卖二十五块才不会亏。卖不出去都行,价格是不可能再低的。
甄克凌无话可说,只得再去一家一家费口舌,一次又一次碰壁而归。
一个月后,甄克凌绝望了。他心服口服,自己不是做生意的那块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