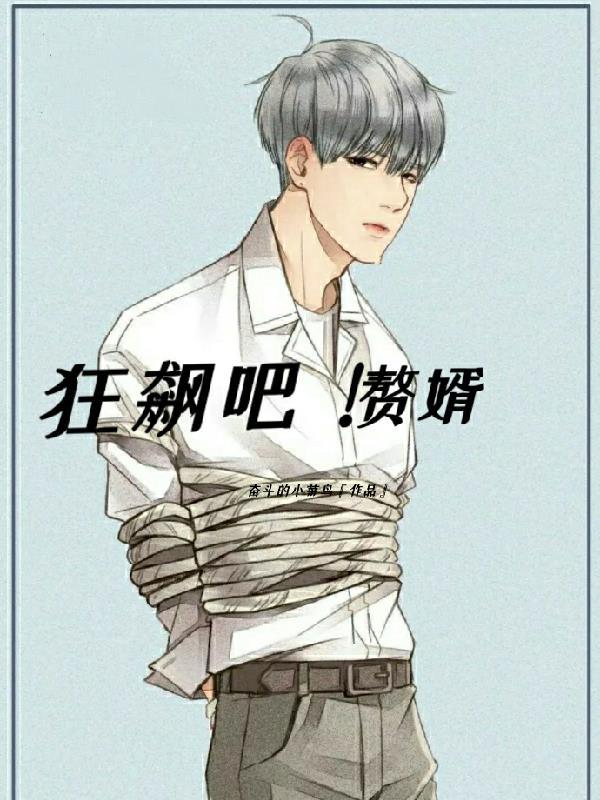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邓布利多太伟大了 > 第1章 山谷(第1页)
第1章 山谷(第1页)
火车上的时间过得飞快,很快,白昼融入了黄昏,一座座灰色的大山耸立在地平线上。夜幕遮盖住窗外景色之后很久,阿比盖尔听到狂风在山谷中呼啸。
对面的阿不思正在阅读着一本厚厚的书,或许是阿比盖尔的错觉——封面上的黑猫似乎正在打呼噜,窗外的声音好像催眠配合着车厢偶尔晃动的声音,阿比盖尔忍不住偷偷打了个哈欠。
这几天的事情多的好像一个梦,阿比盖尔恍惚地想到,她坐在旅馆外面饥寒交迫,突然一个中年男人愿意收养她这个小怪物,又给她买了书本和衣服。
她睡眼惺忪,但是努力睁着眼睛,她看到邓布利多用魔杖从自己箱子里取出一块毯子飘在半空。那条绣着红色花朵的紫色毯子轻轻盖在阿比盖尔身上,“好姑娘,睡会吧,路途太远了。”
阿比盖尔摇摇头,试图让自己保持清醒,困意就像是一团棉花把她包裹着:“这太像一个梦了。”女孩嘟囔着,“我被人收养了,还被允许以后读书写字。”
她在心里确信无疑地说道,等到自己闭上眼再睁开,自己依旧裹在一团破布里面或者更加糟,她还在那个小黑屋里面,阿比盖尔的心一沉。
在她沉沉睡去之前,她听见一个温和的声音:“现实可不会变成梦境,阿比盖尔。”那声音她一瞬间没有想起是谁,但是她明显被安慰到了,于是阿比盖尔披着毛毯在火车上沉沉睡去。
火车似乎没过一会就停下来了,阿比盖尔从毛毯下面探出脑袋:“早上好,先生……父亲。”她睡眼惺忪。
车厢里的灯晃动着,借着灯光,她看清对面的阿不思正在挥舞着魔杖让东西排队走回他的箱子里:“晚上好阿比盖尔,有没有做个好梦?”
阿比盖尔点了点头,她歪着脑袋看着这些,无论什么时候看到魔法出现在自己面前都很让她惊奇,她把自己身上的毯子迅叠好,然后看着毯子扭捏地朝她鞠了一躬跑回箱子里。
阿比盖尔以为他们会跟着人群一起出站,但实际上邓布利多只是看了看自己的怀表,然后掏出一个糖罐子让阿比盖尔和他一起握住它:“六点十七,看来我计算的不错,时间正好。”
阿比盖尔有些奇怪,一开始没有生什么,邓布利多一只眼睛看着他的怀表:“三,二,一……”
说时迟那时快,阿比盖尔觉得似乎有一个钩子在他肚脐眼后面以无法抵挡的势头猛地向前一钩,她便双脚离地,飞起来了。
她能感觉到,或者说看到邓布利多在她身边淡定地将怀表放回自己口袋,阿比盖尔的手指紧紧抓在糖罐上,然后——
她的双脚重重地落到地上,面前的一切在她面前旋转。她想抬脚走路,但是自己的双腿仿佛不听她使唤一样左摇右晃,阿不思用一只手拉住跌跌撞撞的阿比盖尔防止她摔在地上。
阿比盖尔抬起头,看到阿不思的头上的那顶帽子还安安稳稳地坐在主人头上,阿不思收回糖罐子:“是我的错误,你年纪太小了,可能门钥匙还不够稳定,要不要吃点糖?”阿不思又掏出一把糖果,阿比盖尔开始真的担心这位先生的牙齿状态了。
“不,没有,我只是有些激动。”但是她还是拿了一颗粉色的糖果,毕竟糖分永远不会让人失望。
吃了一颗糖后,阿比盖尔觉得自己舒服了一些,这时候她才现两个人正站在一条巷子里面,头顶上是深蓝色的苍穹,几颗星星闪着微光。
阿不思给两个人的箱子施展了“轻如鸿毛”,在去弟弟家前,他还有个地方必须去一趟:“阿比盖尔,你害怕墓地吗?”
阿比盖尔脑中突然闪过一些黑色的,矮小的土堆,其中一个让她心碎:“当然没有,父亲,实际上,我觉得我很喜欢那里。”
似乎是担心邓布利多误解,阿比盖尔补充道,“墓地里很安静,我以前经常和我的朋友去那里看书。”对她而言,人们似乎在墓园里,在那深深的黑暗的泥土下才是真正平等且毫无隔阂的。
而阿不思只是叹了口气,声音很轻,几乎融化在清风吹拂中。他们两人提着箱子穿过教堂边的小门,阿比盖尔跟随邓布利多穿过一块块黑乎乎的墓碑,最终在一块花岗石墓碑前停了下来。
借着星光,阿比盖尔看清这块墓碑的名字:坎德拉·邓布利多,生卒日期底下是及女儿阿利安娜。
阿不思放下一束花——橙黄色的天堂鸟,他细长的手指轻绘着墓碑上的字,“妈妈,安娜。”他在心中轻声说。
而阿比盖尔只是站在后面,邓布利多转身看到女孩手上多出一个花环,看上去很可能是在他不知道的时间里编好的,这让他有些惊讶。
阿比盖尔能感受到邓布利多那一瞬间的悲伤,这让她迫切地想要做什么,最终她催生着墓园里已经枯败的野花编了一个花环。
但邓布利多没说什么,只是让女孩学着他将花环放在墓碑下面,紧紧挨着那束天堂鸟。邓布利多想起这些花是哪里来的了,戈德里克山谷常见的野花,那个夏天,他的妹妹阿莉安娜曾经是怎么抱着那些野花微笑。邓布利多微微闭了闭眼。
最终他们两人站在老宅前,邓布利多轻轻敲了敲门,没人回应。
他试着再敲一次,门被打开了——门前昏暗的灯下,一个同样红蓝眼的男人站在那里,只是他看上去有些不耐烦。
两双一模一样的蓝色眼睛对视着,仿佛是在无声地较着劲,最终男人让开了:“进来吧。”他声音沉郁,而阿不思只是点了点头抬起箱子走了进去。
整个邓布利多老宅似乎是浸泡在一种名叫尴尬的药剂中,他们三个人一人一张椅子地坐在厨房圆桌前,“我的弟弟,阿不福思·邓布利多。”
阿不思先开口,他无视了阿不福斯的冷笑,紧接着继续和弟弟介绍起阿比盖尔,“这是阿比盖尔·阿莉安娜·邓布利多。是我在信里和你说过的,我在伦敦乡下收养的女孩……”
他的话被阿不福思放下茶杯的声音打断,阿比盖尔有那么一瞬间感觉对面那个人有些像烟花,那种只要一点火星就会迅爆炸的那种,她看向阿不思,男人的脸上依旧保持着平静。
“阿莉安娜,哼!阿莉安娜,我真感谢您居然还记得这个名字。”阿不福思冷漠地说道,他的眼睛冷漠却又锐利,“多亏了您还能想起来,为了你那伟大的梦想,抛下了自己的妹妹,最后跑去霍格沃兹当了教师后。现在,十年后,你带着一个大善心带回来的女孩回来,然后还给她取名阿莉安娜,嗯?我是应该夸奖你富有善心还是该说你只想麻痹自己?”
“我从来没有忘记安娜……”阿不思温和地说道,但是他的眼睛有一瞬间看向了茶杯,“我收养这个孩子是因为我不想再看到一个孩子遇到和安娜一样的事情。”
“所以你就给她取名安娜?她就是个……”阿不福思拍着桌子站起来,他的眼睛朝阿比盖尔扫视了一下,看到女孩害怕地抓紧自己的裙子后又坐了回去,“她看上去一点也不开朗,甚至也不勇敢。”男人嘟囔着说道,他最后起身把厨房里的锅盖子打开。
香味一瞬间传满整个厨房,阿比盖尔很可耻地现自己已经饥肠辘辘了。她按住自己的肚子,希望别出咕噜咕噜的声音,阿不福斯则是给三个人分别装了一碗玉米汤。
阿比盖尔的那碗看上去最多,而阿不思的看上去似乎少了些,阿不福思冷漠地说道:“锅里还煮着番茄牛腩,如果你真的关心这个小不点的话就别再往里面放那么多糖。”
“我知道的。”阿不思温和地说道,他搅动着自己碗里的勺子。
阿比盖尔喝着自己碗里的玉米汤,想起火车上阿不思对阿不福思的评价:“我的弟弟,他虽然有些暴躁粗鲁——但是人很好,也比别人优秀的多。”
她绝对不会说是她现玉米汤实际上被阿不福思做的的确有些甜的原因,当然阿不思肯定也现了,等等——阿比盖尔决定假装看不到阿不思又往汤里面放了好几勺糖这件事。
阿比盖尔的房间在阿不思旁边,她的小箱子里只有两套换洗衣物,还有两本书。阿不思在检查过她房间后就一直在自己的房间没出来过,阿不福思在她入睡前来过她房间一趟,男人手里是一个大水罐和几个杯子,里面倒出来的似乎永远是温水。
阿比盖尔礼貌地和这位刚刚把她吓到的先生道谢,“你倒是礼貌。”阿不福思很不客气地说道,“是阿不思给你写信告诉我的,说你岁数很小,这点倒是没骗我。”他一开始以为这个女孩只有五六岁,她看上去比空中摇晃的芨芨草还要瘦弱。
“我想我哥哥告诉你,一直到来年三月你都会和我一直住一起。”
“我知道的先生,父亲在火车上告诉我了。”
“他就和你认识了不到一天,就跑去伦敦魔法部人口记录册把你的名字和邓布利多写在一起。”阿不福思短暂地哼了一下,他看上去有些生气,“我不明白阿不思为什么已经收养你了,还要对你这么冷淡。”还没等阿比盖尔回答,阿不福思便走了出去。
阿比盖尔坐在床上,她思考着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想到阿不福思愤怒的样子,她再一次后悔自己的嘴巴不像孤儿院的其他孩子那般灵巧。
她有些惶恐,想着自己的存在是不是为这对兄弟增加了隔阂,她把被子拉到自己下巴下面在床上胡思乱想着。阿比盖尔以为自己很晚才会睡着,实际上很快就陷进了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