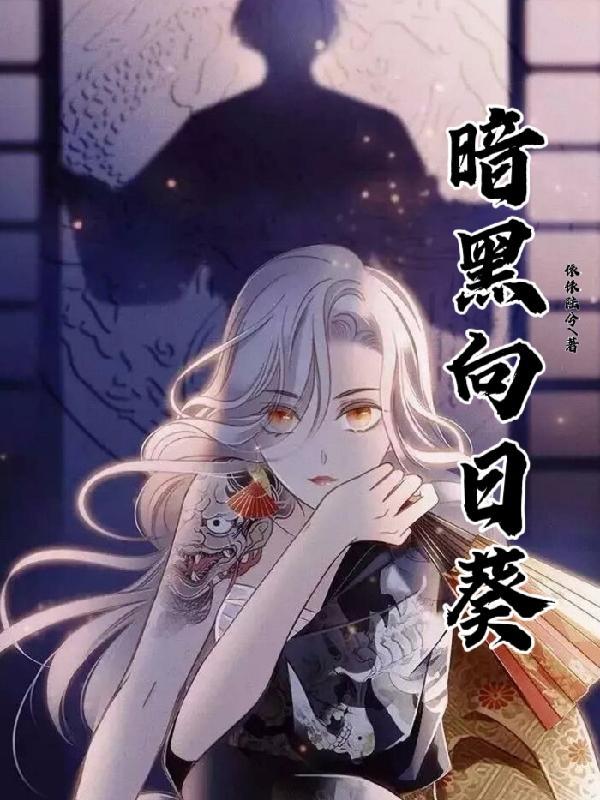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俯首称臣by杀了这个神 > 第172章 迷药巴戟天(第2页)
第172章 迷药巴戟天(第2页)
“该死,中计了。”
压抑的怒意顷刻爆发,他抬手按住自己的额头,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但他已经快要失控。
那酒气中混杂着一股奇异的药草香,这酒和菜都被动了手脚!
陈晞想起方才家丁送酒时的情景。他们的眼神让自己觉得奇怪,那不是唯唯诺诺的胆小怕事,而是在点头交换着信息,应该是熟练无比的杀手。他的视线一凝,脑海中迅速浮现一个答案——野生巴戟天。
这种南边山谷里的稀有药草,瘴气可怖,除了采摘圣手,其他人根本无法近身就已经落得一身病痛,或是失明。这味药,甚至不必服下,单是嗅其气味便能让人迷情乱神。但如果食用,那效果必然更加剧烈,这也是此时沈暮白比自己还要混乱不堪的缘故。
这两人应当是偷摸进来的,扮成和郝府家丁的模样,为了给自己下药……他们查案到此地,想来是行踪被出卖。没想到这只黑手,已狂妄到伸向自己了。
然而今日丑时、郝府,更是沈暮白与疑点重重的保州刺史廖腾所约定的见面地点与时辰。
“中计?”
沈暮白还是乐呵呵地笑着,完全没有意识危险正在靠近。然后,她便在几案上昏睡了过去,但嘴巴还嘟嘟囔囔在说着什么。
微弱的月光透过窗棂洒在沈暮白的纤薄背部,映得几案上的酒盏都微微发亮。那迷乱的野生巴戟天的气息,在屋内乱窜,生怕有什么人会侥幸被他们漏掉,绝不允许任何人在他们的鼻息下安然无恙。
“我……觉得好热,好难受……”
沈暮白时而清醒,那无助让人心疼。陈晞徒手撕下一块衣料,掩在自己的鼻口上,强迫自己不能被迷药惑乱,时刻清醒着。
“无论是什么人,先过我这关。”
他几乎耗尽全力,咬着牙,用最快的速度,先是吹灭了屋内所有烛火,再使出上半身的所有气力挪动自己的四轮来到门口。他用身体挡住门,将门闩死死拴上,然后将携带的佩剑“啪—”地抽出,在暗夜中随时待命。
果然,没过多久,门外传来几声娇滴滴的女声,带着刻意的甜腻。
“殿下,我们姐妹几个是来伺候您的。”
“请殿下开门。”
叽叽喳喳,那声线柔软得仿佛能滴出蜜来,门却被拍得震天响,从轻到响。
果然不出所料,有人要将他今夜困在此处,专程派来烟花之地的女子,为迷惑人心而来,又用稀有的野生巴戟天加持,好让他在倡楼绮户的梦中纵横交错,忘了自己肩负的责任和本性。甚至可能,他们会在夜半十分潜入,直接杀了自己,抹去一切痕迹。
见鸦雀无声,屋内暗淡,门外的拍打声逐渐平息,四周安静下来。
陈晞于是深吸一口气,他的视线又扫回屋内。只见她早已昏昏沉沉地闭上了眼,身体却在几案上摇摇欲坠。
他赶忙将轮椅推近扶住了她,他伸出手来抱住她。衣衫下的脉络已然充血,他的线条骤然绷紧。素日里他的脸庞骨肉恰到好处,又加上衣衫宽松,掩去了轮廓分明的好身形,但此刻那蕴藏的力量爆发出来,仿若蛰伏许久的猛兽,一触即发。小臂上的筋脉凸显,连肌肉的起伏都清晰可见,每一次用力,都让他的肩背像是被一根弓弦拉到极限。他双手用力托住她的腰身,双臂肌肉隆起如铁石般坚韧,硬生生地将沈暮白抱离,将她安置在自己的床榻上。
他毕竟是不具之人,只好使出残存的上身力气,额头上早就布满冷汗。但刚刚用力时,他分明发现了自己的双腿在不停地颤抖,这是向好的征兆吗?
他将一旁的被褥拉过,盖在她的身上,为她轻轻盖好。
沈暮白在枕上双眼紧闭,但扭来扭去,总觉得不舒畅。陈晞的视线落在她的脸上,她的神色稍许平静下来,但红晕依然未退,扭动幅度愈发增大。
他只觉得自己腰间一阵酸涩,先前自己的两手掌心牢牢托住那纤弱无骨的腰肢,身子承载的重量比往日更重,但那份炙热与柔软让他一时无法分辨,是酒意熏人,还是唯有眼前的人会让滴酒不沾的他酩酊大醉。
垂下的眼睫间,他的眸色暗沉,像是深潭一般无底,又不敢松懈。
沈暮白在床榻上酣睡,嘴里含糊不清地咕哝着。
“皇弟,你这……满堂清客,竟不见一尾灵鱼随盏而欢,岂不索然?”
说罢,她咯咯地笑出声,肆意又洒脱,这世间的阴谋像是都与她无关。
“这么多酒……陈晞你怎么都不喝,喝啊……喝啊……”
说着她又睁开了那迷离的双眼,在床榻上直起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