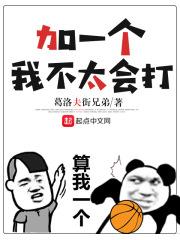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重生之长公主gl洬 > 第64章 我不能放弃他(第1页)
第64章 我不能放弃他(第1页)
“殿下……”
“几时了?”她打断栉巾的话头,轻声问道。
栉巾赶忙去看漏刻,恭敬回禀:“亥时一刻了。”
她似乎松了口气,喃喃自语:“还有不到一个时辰,就快了。”
突然,殿门洞开,从里面走出了一个矮矮胖胖甩着白拂尘的人。
是玉内监。
楚长欢的眼睛只亮了一瞬,又重新黯淡下去。
玉内监小跑着走到她跟前,弯了弯腰,急切道:“殿下您这是何苦呢?即便是真真儿等到了子时,陛下也是不会同意您的请求的。”
她摇摇头,努力勾起唇角,回了他一个笑模样:
“总要试一试。更何况,朝令夕改,不是父皇的风格。”
“殿下……”
“我是他活着的唯一希望了。”
她的目光虚置在昭乾宫的大门上,那里面似乎有灯火闪烁,但很远、很模糊。
“我不能放弃他。”
……
其实,在这夜以前,她只是知道自己喜欢沈故言,却从不知道自己究竟喜欢他到什么程度。
有句俗话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他们甚至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夫妻,所以,对于生来高贵的楚长欢而言,她似乎从不会认为,这世上会有那么一个人能让她心甘情愿地付出所有。
可她低估了沈故言对她的吸引力,也低估了自己对沈故言的感情。
跪在雪地里的那两个时辰,她不停地想着他们之间曾经经历过的一点一滴,她想要剖析开沈故言这个男人,她想要知道他究竟怎样的魔力,才能让她心甘情愿地抛弃所有,以死明志,来换他的一条生路。
可后来她却不敢想了,这两个时辰比她想的要长得多,她苦熬着,似乎是熬过了一辈子那样长,她怕自己想的那些过去,就是所谓的“走马灯”。
传说中,人死前才会看到走马灯,再走马灯里重走一遍来时的路,然后人死灯灭,气息全无。
她虽然不怕死,但却并不想死。
如果死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昭皇或许还会把她的死归咎到沈故言的头上,她不想死了还要来拖累他。
只有她活着,他才能活。
……
思绪变得模糊不清,她似乎又坐到了醉春烟里,临窗拈花,等着从府里出来的他。
画面一转,她又坐到了烟雨朦胧的孟良江上,扁舟里,他为她抚琴,琴音和江水的浪头声混在一起,宁静旷远。
她似乎听到了钟声。
孟良江畔,有寺庙吗?她怎么不知道?
“殿下,子时了殿下!”栉巾和掬水几乎是同时朝她跑来,她皱着眉头勉力回笼思绪,眼前的画面却依旧定格在那艘小船上。
如果这辈子都能留在这儿,也挺好的。
她笑了起来,如花的笑靥却因为她唇角不断渗出的鲜血而变得诡异,血滴一点一点地打在雪地上,就好似雪中生花。
腹部一紧,她呕出一口鲜血,昭乾宫的殿门应声而开,昭皇穿着整齐地站在门前,震惊地看着雪地上那一大片惹眼的红。
眼前终于清明起来,她脱力摔在地上,看着那个明黄色的身影三步并作两步地往下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