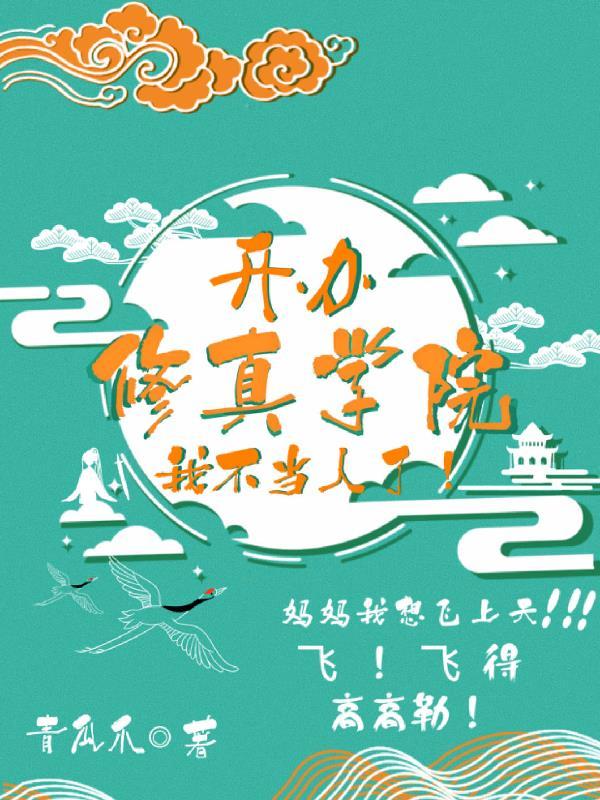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衣冠禽兽在古代代表的是什么 > 31 全不在乎在父亲的灵堂上做出的言行(第1页)
31 全不在乎在父亲的灵堂上做出的言行(第1页)
男人拽着女孩的头发,将她按到自己胯下,阴茎塞入女孩口中,狞笑着说:“想喝我的尿,是不是?给你,都给你,老师的小尿壶,肉便器。”然后,腥臊的尿液便从男人的阴茎口涌出,灌进了女孩嘴里。
越柔顺、越婉媚的女孩,越会激起某些男人的施虐欲。
如姐姐这般,身体骚浪,心理沉沦,又畏惧服从强权的女孩,是施虐癖最喜欢的下手对象。他们虐待女孩,还要女孩身心顺服,感恩戴德,仰他们如神明。而两姐妹被男人调教这么久,早已身心扭曲,被塑造成男人想要的模样。
于是,姐姐几乎是欢喜雀跃、迫不及待地含住男人的阴茎,将苦涩难喝的尿液一口口饮净,又依依不舍地吮住男人的龟头,又舔又吻,爱不释手。“主人,主人……”她看着眼前的阴茎,神情难掩崇拜,“好厉害啊,好喜欢……”
女孩的心中,难以自抑地浮起对男人生殖器的喜爱。
男人将女孩按在身下,扇乳摸屄,仅凭几根手指,就玩得女孩飘飘欲仙,蚀骨销魂。男人的动作并不怜惜,甚至十分粗暴,但女孩早已习惯被如此对待,甚至能从男人轻贱暴力的言行中,品尝出别样的快感。
女孩被男人的荷尔蒙笼罩着,鼻尖尽是男人富有攻击性的体味,只觉灵魂都飘荡起来,快感如同潮水一般,一波波在她体内冲刷,带着淫液源源不断地涌出体外,流过沙发的表面,在地毯上洇出大片水痕。
直至日落西沉,天色渐晚,男人才终于结束这场淫虐的玩弄,女孩早已神志昏沉,几乎在男人松开她的一瞬间,便沉沉地陷入了睡眠。她的嘴角挂着满足而安宁的笑意,脸颊酡红如烧,清媚美丽,风情婉转。
男人身心餍足,懒洋洋地从沙发上站起,却注意到妹妹跪坐在地毯上,怔怔地望向他们,眸色复杂。男人挑起眉头,“嗯?”了一声,妹妹像被惊醒一般,立刻回神,慌乱地垂下眼眸,小声叫他:“老师……”
男人点头,又问:“在想什么?都出神了。”
妹妹犹豫一下,才轻声说:“刚才,老师看起来,好喜欢姐姐呀。”她说不清自己内心的滋味,有点酸楚,有些怅然,更多地却是某种理所应当的宿命感。当然啦,姐姐那么漂亮温柔,听话乖巧,又沉迷性爱,喜欢疼痛,无论被怎么对待,都能展现出柔媚多姿的风情,且不像自己这般拧巴。老师会更喜欢姐姐,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可是,还是会有些……在意呢。
当老师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离开,完全放到姐姐身上时,她依旧会感到失落与酸涩,明明知道不该如此,却无法抑制。
妹妹垂下头,膝行到男人身边,抱住男人的身体,软软地依偎着他,眼神迷茫,神态怅惘,轻声说道:“我好坏啊,竟然会感觉到、感觉到……”她咬住下唇,仿佛难以启齿,却仍然勉强自己,对着男人坦诚心怀,“……感觉到嫉妒。”
女孩羞愧地低下头,讷讷道:“对、对不起,老师,您惩罚我吧……我知道,这是不对的,我只是、只是……”她说不出来,男人倒是了然一笑。他半蹲下来,望着妹妹的眼睛,柔声道:“你只是喜欢老师,所以会不由自主地在意,对不对?”
女孩闻言,怔怔地看向男人,仿佛被说中了极隐秘的心思,一时间心中又是酸楚,又是感动,酥颤难言,“……对,我太喜欢老师了,好爱好爱您,所以总希望您的目光……能长久地放在我身上。”女孩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抚摸着男人的脸颊,痴痴怔怔,“我知道,姐姐也很爱您,也希望得到您的关注,我不该这么自私,但是……”
男人握住她的手,放在嘴边亲了亲,笑道:“没关系啊,这种嫉妒和在意,正是你爱老师的证明。不用克制它,去品尝它,体味它,仔细地感受它,每次有这种感觉时,你就会知道,你正在爱着老师。”
“品味这种感觉的过程,也是体验爱情的过程。即便酸楚,即便痛苦,它也是美的。”男人笑得温柔,眸光深情脉脉,说着动人的情话,却又透露出难言的蛊惑,“你不会因为这个,去伤害任何人,不是吗?体会这种感觉,只是自己的修行,别害怕它,要欢迎它,将它当作爱情的外在体验,好好迎接它。”
男人的谆谆细语,抚平了女孩内心的仓惶,也让她更加沉迷男人的温柔。她软伏在男人怀里,乖乖点头,柔声道:“我明白了,谢谢老师。”然后,她似是有些不好意思,含羞笑着抬起脸来,又说:“不过,还是请老师惩罚我吧。我今天高潮了好多次,享受过淫贱的快感,该被老师狠狠责打,用疼痛训诫。”
面对女孩柔情款款的请求,男人自然欣然悦纳,却又说:“好,不过这个不着急,可以等一等。”女孩问:“那要到什么时候?”男人扬眉一笑,意味深长道:“自然是,等你们父亲回来。”
两日后,凌先生与凌太太的骨灰跨越千里,终于被送回凌家。
在男人的主持大局下,凌家已布置好灵堂,逝者的遗照摆在正北,堂内黑幡白纱,菊花装点,庄重而肃穆。葬礼为期三天,吊唁会持续两日,第三日傍晚吉时,骨灰入土下葬。
凌先生生前交游广阔,接触的政界官员、生意伙伴、下属雇员数不胜数,因此来往宾客众多,堂上川流不息。他们带黑纱,着素服,沉默庄重地送上挽联,对凌家仅存的两位小姐温言劝告,请她们“节哀顺变”、“保重身体”。
因涉及的利益纷争均已平息,诸事尘埃落定,因此葬礼之上,并无其他纠纷,只是按照习俗礼节,顺利地走完流程。凌氏姐妹身着黑色丧服,对每一位吊唁宾客鞠躬致谢,面容平静,举止得体,并不过分悲痛。
众人不以为奇,他们均知,凌氏姐妹已继承凌家全部财产,将来富贵傍身,衣食无忧,自不必过分悲痛伤怀。商场浮沉许久,他们见多识广,知道在葬礼上最痛苦的,往往是最依赖死者之人。若死者逝去后,他们前路迷茫,便必定悲痛万分,但若后路已定、终身无忧,那即便伤痛,也多不会失态。
他们以自身的社会经验,揣度凌氏两位小姐,却不知道两姐妹性情单纯,并无这些心思,她们举止自持,情绪平静,只是因为与父亲感情平平,早已疏离,于后母更是疏远漠然,全不在意。
她们内心的所有情感,都已寄托在男人身上,如火如荼,热烈灼烧。这份过于炙热的感情,焚毁了其他情感,斩断了社会亲缘,让她们一心只系于男人,再无瑕关注其他。
男人仅用短短几个月,就将女孩的身体与心灵,从她们的原生家庭完全剥离。恰逢亲人去世,外有豺狼觊觎,内无他人可依,两个女孩孤立无援,更给了男人绝佳的机会,温言引导,细语蛊惑,让两个女孩浑然忘记一切,眼里心中只有男人。
以致即便是在父亲的葬礼上,她们都能如局外人一般,从容应对。
甚至,在女孩们及地的黑色长裙之下,仅有光裸的双腿与挺翘的臀丘,连内裤都未曾穿着,只因为男人说:“仪式结束后,就将依依的惩罚,放在灵堂吧。”
男人的手段,实在是……高超缜密,令人胆寒。
如此深沉心机、高明手腕,两个未经世事的女孩,如何与之抗衡?
于是只能沦陷,自以为的心甘情愿,不过是男人的步步为营,如此罢了。
吊唁结束后,两姐妹按照习俗,需要留在灵堂,彻夜守灵。
但灵堂空旷阴凉,又有黑白遗照,烛火飘摇,宾客离开后,就只剩下森寒的冷意。两个年轻的女孩,温婉胆小,如何敢自己守在灵堂?自然是哀求男人,求他留下来陪她们。
“我留下来可以,但之后要做什么,可都得听老师的。”男人笑道,目光不怀好意。
女孩们明白男人的意思,却都两颊微红,羞涩垂眸,妹妹嗔道:“老师要做的,我们什么时候拒绝过?在哪里都行,这里……当然也不例外。”姐姐笑道:“我们听话的,老师说什么,我们便做什么。”
男人勾起嘴角,语气微沉,“即便是在灵堂上,你们父亲的面前,当最下贱的婊子?”
他的声音里,透出危险的欲望。姐姐听得身体燥热,竟觉出几分背德的快感,她咬住下唇,轻声说:“我本来就是老师的婊子,就算给他看着,又能怎样?主人疼我,我高兴都来不及,才不在乎他呢。”
这个“他”,自然是指代她们的父亲。
妹妹也说,“老师说过……要在这里惩罚依依的。”她含羞带怯,又难掩期待,似乎全不在乎在父亲逝后的灵堂上,做出淫乱放浪的言行,亦不觉得这种事情可耻荒唐,应被唾弃。
她们的价值观已被扭曲,世俗的伦常不再能约束她们。在她们心中,唯一至高无上的,只有男人,剩下其余,都已毫不重要。
只要是男人的心意,她们都会遵从,无论时间、地点与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