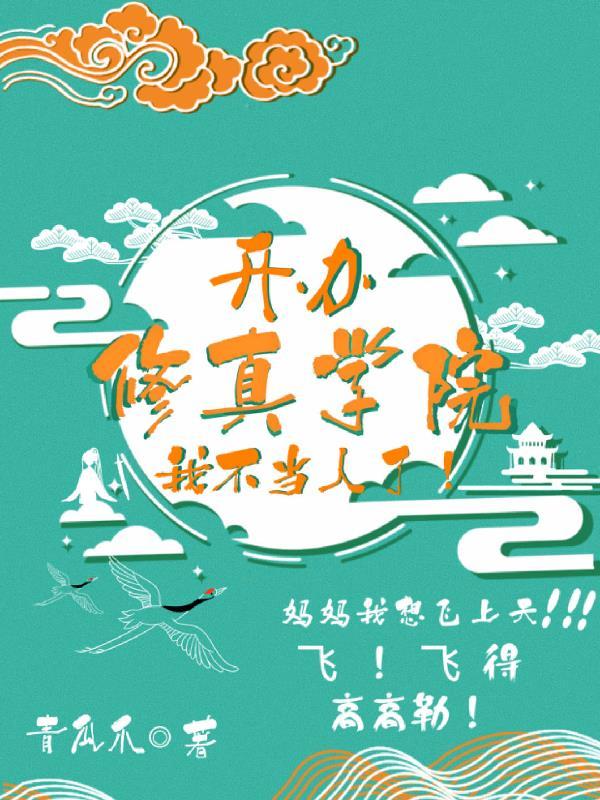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捡了个姑娘夫兮 > 第25节(第2页)
第25节(第2页)
秦霁想起了那本金陵游记所录,江南庙会与京城的庙会略有不同。
其一便是名目。
京城的大相国寺为了货贩生意,每月开市五次。
而江南因着巫神之说成风,则借神诞的日子举办庙会,大大小小的道君,菩萨,轮着番过生,庙会跟着一场接一场。
每逢神诞,便会有商人趁此良机在庙前开办大市小市,游客在庙中烧完香后又能逛市游玩一番。
绿珠问秦霁:“姑娘你看过瓦官寺去年的庙会么?”
秦霁双手撑着腮,摇摇头,抬眸时露出一缕疑惑。
“瓦官寺,是个很大的寺么?”
绿绣在一旁道:“瓦官寺是前朝留下来的旧寺,说小不小,但也谈不上大寺庙。要说金陵城中的大寺庙,头一个便是先帝下令在这儿建成的大报恩寺,其次便是定林寺,毗卢寺。这些寺庙都要比瓦官寺大。”
前朝的皇帝笃信佛教,都城还是在这金陵,江南各地为了迎合圣意大肆兴建起了佛寺。
曾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里的寺庙果真有很多,漫长的九年过去,能保全名姓留在秦霁记忆里的东西实在是少。
“原来是这样。”秦霁微微一笑,又问绿珠,“去年的瓦官寺怎么了?”
绿珠说了这么久,没见秦霁丝毫不耐,而是一直在认真地听。这让她受宠若惊,放下了先前那一点儿害羞,转头说得更加来劲。
“去年夏,我在那儿看的城隍庙会,便有一出钟馗嫁女。那钟馗站起来还没有他妹妹高,衬得妹妹都有些魁梧了,这二人动作利落潇洒,还改了词,很是有趣,只是可惜他们没演完就换了人。”
“说得我也想看看了”秦霁眨了眨眼,似是羡慕。“你去年就来了这园子么?”
“我与绿绣姐姐皆是四年前来的这儿呢,是国公府的家生子来的。”
秦霁点了点头,回之一笑。
不知不觉天黑了下去。
陆迢今夜没来。
秦霁上床后茫茫然睁着眼,绿绣给吹灯前看了看她,小声说道:“姑娘若是想看庙会,不如同大爷说,他说不定会带您去呢。”
秦霁“啊”了一声,从床上半撑起身子,“那我能自己出去看么?”
她忍得住不问陆迢,却忍不住不问这个。
绿绣立时慌了,摆手道:“这可不行,大爷交代过了,姑娘是不可以自己出榴园的。”
忍了好些天,得到的是一个意料之内的答案。
“我好想大人。”秦霁对着绿绣念了一句。
随后不看她的反应,认命地躺回床,合上双眼。
绿绣提着灯笼走了出去,房门卡哒一声合上后,竹阁里便只留下满室幽暗。
秦霁重新睁开眼。
绿珠说的那些街巷名字,她只对其中一二稍有些印象,还是在家中偶尔与父亲闲聊时提到的。
她与父亲之间,除却那段往事,提及金陵的次数实在是不多。
秦霁凭着刚刚听到的那些,在心中粗糙描绘了一个金陵的巷道走向。
榴园是在城西的延龄巷,往东便是城中的主街……
*
第二日,应天府署的狱房最里。
如兰和照升关在相邻的两间牢房,一连多日,除了送饭的狱卒外再无他人踏入此地。
牢房墙沿最上有一个拳头大小的眼窗,天稍稍阴一些,里面便暗得分不清白天黑夜。
墙下堆着积久未换的箍拢草,不知多少人在这上面躺过,上面的血污脏垢实在太多,已经看不出这草原本的颜色。
受了潮,便往外发散着令人溺毙的腐臭。
照升卧在这堆湿扁的干草之上,被这股腐臭死死压着胸口,越压越沉,他猝然睁开眼,猛地咳嗽起来。
另一边的如兰即刻揪起了心,扶着木栏往他这边查看,眼泪止不住的往下落。
“照升哥哥,对不起,都是我连累了你。”
照升咳完平复了一阵,起身到隔着两人的木栏旁边,宽大的囚服罩在这个清瘦的十九岁青年身上,入目可见的狼狈惨淡。
照升笑了一笑,憔悴的眉眼重新冒出一点鲜活气,他轻轻揩去如兰眼角泪珠。
“说什么傻话呢?此事与你能有什么关系?是我没用,不能带你走。”
“不……不怪你……照升哥哥。”如兰哭得更加伤心,连声哽咽起来。
怎么能怪他呢?
如果不是因为要救自己,照升哥哥不会伤人起事,他书读的好,一次便考中秀才,还是里头最厉害的廪生,再过几月便是三年一度的乡试,举人必然也是囊中之物。
他这时本该在书院读书,为奔向以后的大好前程而努力,而不是陪着自己在这暗无天日的牢狱当中苦等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