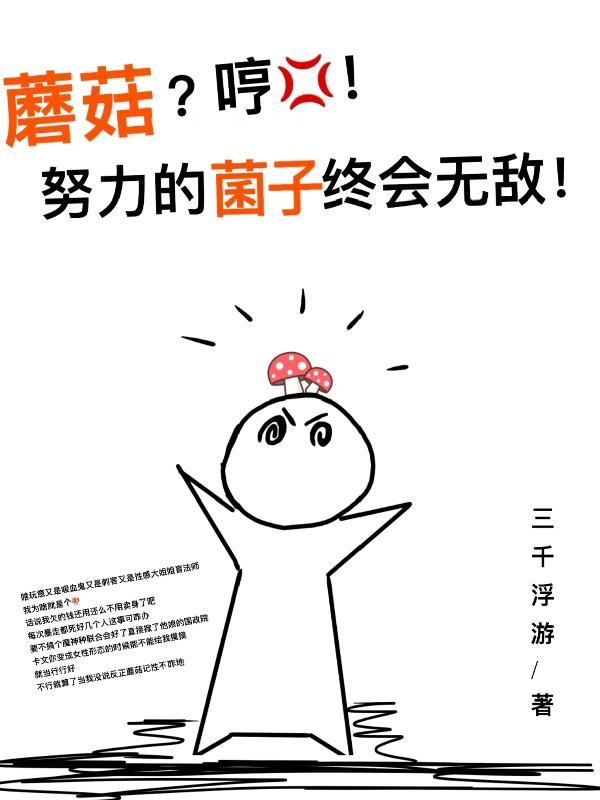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三盏灯怎么接线 > 分卷阅读26(第2页)
分卷阅读26(第2页)
这份无可救药的爱就这样到来,在这之前他甚至没有思考过自己爱男人的可能性,而余书缘就存在在那里,好像注定就是要被人爱上,从而奉献出自己的一切的。他从没有为谁如此癫狂、又如此彻夜不眠过,这种异常如果是因为感染了名为“爱”的病毒,他简直要为此得恐惧症。
然而他又无比庆幸——他这样无可救药地爱上余书缘了。如果没有余书缘,贺云恐怕会冷淡地过下去,不咸不淡地过完自己的一生,在年老时对别人狂热的恋爱嗤之以鼻,完全不知自己有多可悲。
因而当余书缘问他后不后悔时,他决心一定是不后悔,绝不后悔。哪怕离婚鳏居两年,他从没有一刻忘记过余书缘,也没有一刻停下思念他,他将和余书缘分开的事当作要用一辈子去消化的议题,必须如此,才会好受一些。贺云根本无法接受余书缘或许不爱他、又或者不那么爱他的可能性,因为如此,他才毅然决然地同意离婚;因为如此,他才打定决心永远不要回头。哪怕带着思念固执地活一辈子,他也绝不要回去接受余书缘或许不爱自己的事实。
“什么时候。”贺云哑声问。
“你说,”余书缘忽然笑了一下:“你问我,要不要吃那个特大份炸洋芋,多醋多辣多折耳根的时候。”
——余书缘这人简直太过分了。
贺云低头看着他,眼泪一滴一滴落在他脸上,余书缘想伸手替他抹泪,被贺云伸手推开。为了掩饰自己的丢人,贺云立刻起身走进卫生间。余书缘快步走上前来,在卫生间外面大声说:“贺云,出来抱我!”
贺云猛地拉开门,直接揽住那人膝窝,将人往肩上一扛,三步并作两步扔回床上。
“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不早说!”
贺云恶狠狠地掐他的脸,把脸蛋肉掐得变形。
“你…”余书缘艰难地说:“你脾气特别臭,你这个臭石头!”
“你还好意思说我。”
贺云气不打一处来,将人翻过去按在腿上,裤子一扒,照着光洁的臀就是“啪啪”两巴掌。
“啊!”
余书缘毫无防备挨了两巴,心里脆弱得紧,嘴上却依旧不饶人:“别打了!你家暴我!”
“哦,这就叫家暴。”贺云冷冷地说:“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的家暴。”
说罢又照着圆润的臀“啪啪”两下。贺云常年打篮球,手掌有余书缘头大,结结实实两掌打下去,臀肉立刻红透,火辣辣地着烫,余书缘被打得哭腔都出来了:
“别打…”
贺云见人腰也软了,疼得一抽一抽的,于是又心软得将人翻过来,替他擦泪。余书缘拍开他的手,边替自己抹泪边说说:“一巴掌赔一万,总共四万。”
贺云笑了两声:“行,赔你就赔你。”
将人塞回床上时,才又感觉到不对:“既然如此,那我陪你睡应该也有钱吧。”
“什么钱。”余书缘吸了吸鼻子。
“我陪你睡,这不叫服务吗?”
贺云一笔一笔跟他说:“给你做饭算不算服务,帮你洗内裤算不算服务,这都要收服务费。”
“那一天给你开两百行了没。”
贺云将人抱紧,不甘心地说:“一天就开两百,你打叫花子呢。”
余书缘抗议道:“你陪睡又不是睡荤的。”
“你还懂荤的素的。”贺云大为震惊:“想要荤的早说啊,小爷我也不是不愿意伺候你。”
说罢,边开始对余书缘动手动脚,余书缘边躲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