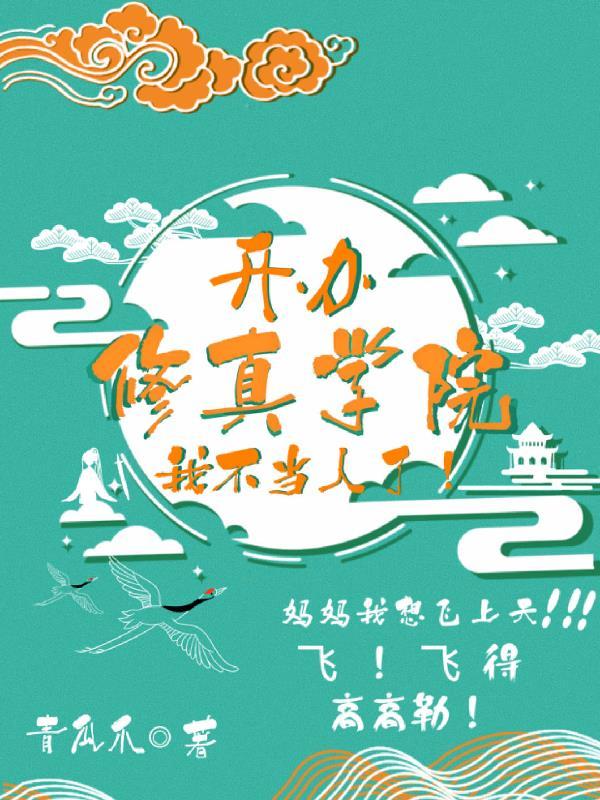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折刃免费阅读 > 第67章(第1页)
第67章(第1页)
她乌发散着,垂下来像缎子,兰烽小心翼翼地抚摸:“那就留着。”
这一世,一切都变了,又没变多少。李亨还是英年早逝了,福嘉不得不为身边的人做打算。
于是她摇头:“穗穗与白禾性子不一样,她早晚是要找个归宿嫁人的。万事讲求时机,我不推她一把,过了这个村,哪还有孔五郎这样对她真心,又年少有为的郎君呢?”
兰烽不置可否。在他看来,穗穗单纯烂漫,能一辈子跟着福嘉,在府里混吃等死,说不定还更开心。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福嘉说得也有道理。
他与她询问了太子登基后的安排,福嘉突然想到:“大皇子和皇后的事,你怎么都不与我商量呢?”
兰烽听着她闷闷的声音,终于忍不住,起身将她从软椅中抱出来。
四目相对,他动作强硬,长臂穿过她的膝弯,兰烽用另一只手固定着她的后腰,将她按在身后挂着绒毯的墙上。他与其额头相抵:“不能脏了你的手。”
福嘉眼圈红了:“你也要爱惜羽毛。”
她用一种平和的语气道:“若有一日,我不在了,墨砚也不做皇帝了,这些事被翻出来,你是要掉脑袋的。”
兰烽将她抱得更紧,没说话。他想,若是福嘉不在了,他是生是死,又有什么所谓。只是这话说不出口,他怕吓到她,所以他只是轻“嗯”了一声:“以后会先同你商量。”
手臂收紧,福嘉有些透不过气。少年身上有一股好闻的味道,清冽干爽,这样的窒息感反而短暂地让她很安心。她把纤细的肩头缩在他肩膀中,炽热的胸膛内,心脏跳动的声音如鼓点般有力。福嘉贪恋地吸了一大口,又有些嫌弃自己的沉溺。
这样好自私啊。
她换了个话头:“你能陪我去看看康平吗?曹家算是败落了,她算于我们有恩,我想看看她过得好不好。”
兰烽想到曹暄鹤的事,松开她,打算去换一件衣裳:“什么恩?”
福嘉垂眸一笑:“在行宫,鸳鸯蛊。你喝了母蛊,大概是那丫头捣的鬼。”
两人见到康平时,她正在外城一座寺庙里进香。一个人进庙,外面带了十几个随侍,陪着进来的还有两个贴身婢子,三个婆子。
婢子扶着她跨过门槛时,看见面前站着熟悉的面孔,康平没有多意外。
她远远瞧着福嘉,习惯性将手放在小腹上,依旧不改一贯的趾高气扬。
福嘉笑道:“哟,二姐姐这次怀的,是不是男宝啊?”
康平撇嘴道:“你送来那神医,说看着十有八九。也不晓得是不是神棍。”
福嘉哼道:“我听神棍说,你赏她的金山银山,柜子都塞不下了呢。”
康平不以为然:“算她运气好吧,治好我先前的病,我就当破财消灾了。”
福嘉见她还是活蹦乱跳的,放心了。她换上一副正经的表情:“二姐,你放心,陛下不会因为曹后和大哥的事,迁怒到你身上,曹枢使他……”
康平挥手打住:“曹家的事,我不关心了。”
福嘉可不依着她,她知道康平嘴硬心软,对曹枢使和几个同辈的兄弟,是挂在心上的,特意凑近了,同她道:“我偏要说呢。曹枢使告老还乡,陛下赐了他在江南一栋大宅子,好多钱,还专门写了个牌匾给他,很风光的。”
康平眼中湿润,她掩饰地动了动嘴,神色不自然道:“哦,那暄鹤、暄亭呢?”
兰烽站在两人不远处,鸦羽般的睫毛遮住了他眸中微动的光泽。接着他听见福嘉口吻嬉笑道:“暄亭总是气陛下,我说不动他,被送去云南了。曹暄鹤呢,因为曹枢使特意来求情,我和陛下商量了一下,决定还是将他调回京来。”
兰烽静静站在一旁,闻言脸色变了变,眸光骤然缩了一瞬。
康平看了他一眼,眼底划过一抹玩味,她扶着后腰,嗤笑道:“三娘子,早在你成婚之初,便有中官在母后那里说……”
她捏着嗓子,学着小黄门的声音:“福嘉殿下这是示弱呢,说不准哪日,东宫那位应天受命,她就不用受这委屈了。”
兰烽心中一紧,望着福嘉。只见她戳了戳姐姐,附在康平耳边说了几句话,惹得康平去推她打她。
“这么好的驸马,我才不委屈呢!”福嘉走到兰烽身边,揽着她朝康平轻笑:“羡慕死你们了。”
兰烽动了动有些僵硬的胳膊,回挽着她。回去的路上,他以为福嘉会主动开口,但是她问的都是环州和谈的事。
直到回了公主府,福嘉坐在老槐花树下的秋千上,她舍不得老树,不会荡得很远,都是轻轻晃动。
他想起送她秋千的时候,是发现她也不是那么高不可攀,是觉得她可怜。
他们正聊着孔五郎提到穗穗时的情窦初开,兰烽突兀开口:
“为什么让曹暄鹤回来?”
福嘉抬起头看着他。
他看上去没有什么表情,像只是随口一问,她于是也公事公办地解释:“世家百年根深,皇族也需要得到他们的簇拥。曹家算是成了墨砚登基为帝的祭品,做事总要留一线,不能做得太绝。”
“而且,”福嘉想到前世曹枢使所为,她终究为那一点点善,心怀感恩,只是这理由兰烽无法理解,她只好把事实摆出来:“曹枢使告老还乡,又配合我们热热闹闹演这出荣归故里,条件就是让曹暄鹤回来做京官,我和陛下商量了一下,不如就顺了他的意思吧。”
福嘉说得断断续续,立在她面前的少年没有插嘴,间或“嗯”一声,示意她继续,他一直在等着她解释出最重要的那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