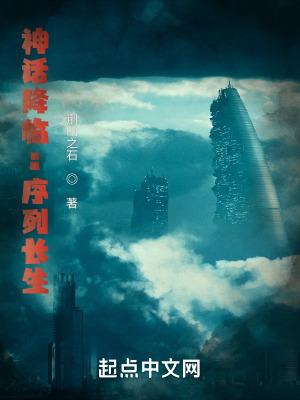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墨染烟华 安婕妤 > 第67章(第1页)
第67章(第1页)
待节度使夫人点头示意,那丫环轻手打开了木匣顶盖,只见其内整齐摆放着各类环钗、玉镯,看来精致秀美。
“这些年,我每年都为知艺准备些少女妆扮物件,只可惜她再用不得了。今日能见得你,属实令我心慰,便从中挑选了几件相赠,望你莫要嫌弃才好。”
为……已故之人准备的物件?
送她?
节度使夫人殷切话语,传入宋烟烟耳中,却令她面上血色蓦退。她匆忙起身,慌乱间甚撞上了那木匣子。
丫环惊叫一声,连退两步方稳住了身形,怨怪地瞥了眼宋烟烟。
“对……对不住,夫人,如此贵重之物,烟烟实不敢收。”宋烟烟再不敢抬头去望节度使夫人,只低垂着头,轻声颤道:“我娘亲独自于院中,我放心不下,还得早些回去,先告辞了。”
谢知珩见宋烟烟此状,对着节度使夫人无奈轻斥了声:“娘,你拿这些物件出来作甚,吓着人家了。”
而后赶忙跨步至宋烟烟身前,歉然道:“宋大人,不好意思,吓着你了。本想留你晚膳的,但……”
“谢公子不必客气,我挂念娘亲,还是早些回吧。”谢知珩于她身前,挡住了旁侧节度使夫人那道一直紧盯着她的视线,她才觉稍稍缓下了口气。
而后,急急往旁侧跨步,垂首福身,定然道:“望夫人安好,便告辞了。”
“哎,好,慢走。往后得空,常来看看我。”节度使夫人口中喃喃念着,缓行至门边,单手扶门,久久凝望着宋烟烟离去背影。
回程马车之上,车厢内静谧尬然,全无来时对谈的自如。
因节度使夫人,言她与故去的知艺形貌相似,且以为知艺准备的物什相赠,她确然有被惊着。但更多的,却是因了“中毒”二字而心头受震。
爹爹当年极为欢喜知艺,知艺在爹爹回京前中毒身亡,而爹爹回京后,也是因了中毒,缠绵病榻两年。
这难道,真的便都是巧合?
或许,有何关联、隐情?
又是怎样的情况,竟会令陇西节度使府,未去追究养女被毒害一事?
她顾自蹙眉沉思,旁侧谢知珩却已然坐立不安,不住在旁低咳着,欲言又止。
谢知珩握拳捂唇又一声重咳,宋烟烟才恍然回神:“谢公子?”
“宋大人,今日对不住,我也未曾想到,我娘她会……其实……其实你同知艺,并无我娘说的那般相似,许是幼时有些相像,但如今,我瞧着,是并无那般像的。我娘她,自知艺去后,大病一场,此后便常年于那小楼清修,恐是……恐是有些忆女成疾,故而有些失态了。”
宋烟烟忙敛了敛神色,回道:“无碍的,夫人忆女之苦,我自能理解。”
宋烟烟所住小院旁侧,元叶疾跑至一条隐蔽的巷子尽头,匆忙敲了敲门,院门启缝,他侧身跨入。
门内是一方宽敞雅致的院落,但他显是无心观赏,径直跑至一间房门前,叩门三下,恭敬报道:“世子,宋大人回程马车已近官坊了。”
房内并无回音,半晌,传来一道刺耳的,瓷器落地碎裂之声。
而后,房门霍然开启,萧京墨于内黑沉着面色而立,地上四处散落着碎裂青花瓷片及各式盐津蜜饯。
元叶垂首不敢望萧京墨面色,整个人因萧京墨此刻的怒意凛然而轻颤了下。
他望了眼地上散落之物,终是闭眼鼓起勇气问道:“世……世子,赵家那封回信,是否……是否可交予小的,递还予宋大人?”
前几日礼部遣人分派京中回信之时,宋烟烟正于窟寺修补壁设,故而由元叶代接了。元叶此前受萧京墨之使,令他关切着宋烟烟院中动向,他便将赵家回信之事如实呈告了萧京墨。
可……如今,赵家托人一并送来的蜜饯已然砸了,那回信总该要……
“回信?赵家何曾回过信?”萧京墨冷嗤一声,讽道,“何为家书?赵家于此官坊内,何有家人?”
萧京墨大步而出,元叶茫然转身,一时无措,只得紧跟着往院外行去。
及至院门处台阶,萧京墨却倏然顿步,沉叹口气,冷然回了句:“待我再思量几日。”
元叶愣然眨了眨眼,见萧京墨出门走远,忙跟了上去。
只是……思量甚?
思量是否将赵家回信,还予宋大人吗?
宋大人如今对世子这番不冷不热之态,世子为何竟还要这般?若然被宋大人知晓了,依她那倔脾气,到时候吃亏的……
马车缓缓停驻,谢知珩再次诚恳念着歉意,望宋烟烟勿要介怀。
宋烟烟几次欲开口相询,问问眼前之人是否知晓更多当年之事,却终归未能开口。
毕竟,堂堂节度使府,竟不追究小姐被毒杀之事,其中隐情……
二人便这般耽搁了会儿,以致,马车停落半晌,仍是车厢未开,无人落车。
“多谢谢公子相送,我便先回了。”宋烟烟终是点头致谢,沉思着,欲起身落车。
可她话音方落,车厢门便被大力由外开启。而后,未及反应,她便被人紧拽着手,撞入了一堵铜墙铁壁般僵硬的胸膛。
腰间被一股极大的力扣了,她整张脸被闷在来人胸膛,只觉了自个儿被人带着跃落马车,却是全望不着人。
但,落地只片刻,她便闻着了来人身上熟悉的清冽竹香。于是,初时的惊惧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一阵懊恼和思绪受扰的心烦气躁。
“放开我!”
身畔被萧京墨气息侵扰,宋烟烟本就烦杂的心绪愈加难抑,身形未稳,便急着双手推拒于他胸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