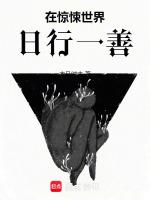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重生桑榆全文阅读免费古代 > 贵妃(第2页)
贵妃(第2页)
这次晕倒,当真是个绝好机会。穆桑榆微微垂,双眸低视,轻轻说道:“陛下,臣妾身子骨不争气,想是染了时疾,怕是要养上一段日子了。臣妾又恐过了病气给陛下,所以吩咐内务府把绿头牌挂了起来。陛下……不生气吧?”
她说的小心翼翼,加之适才刚咳嗽了一通,嗓音沙哑,听来当真有气若游丝之态。
黎谨修看她如此病弱模样,不觉心中一软,遂也放下了身段,一撩衣摆,在床畔坐了,说道:“贵妃既病了,孤便留下,陪陪贵妃。”
说着,又吩咐道:“李德甫,去将孤案头那一摞折子取来。”
“万万不可!”还不等李德甫答话,穆桑榆已抢先一步脱口而出。
“怎么,贵妃这是……不愿留孤?”帝王的浓眉,再度凝了起来。
总归穆桑榆是跟了他多年的老人,是他的贵妃。
他不想为着一个秀女,就和她生出龃龉,她既服了软,自己也想找个台阶下来。
然而,穆桑榆竟想赶他走?直至此刻,穆桑榆方才察觉,自己对于这个男人的抗拒竟到了如斯地步。
不想看见他的脸,只要他在这里,她便浑身不自在。
在帝王凌厉的审视目光之下,穆桑榆垂浅笑,柔声细语道:“陛下,臣妾身染疾病,您在这里,臣妾不能尽心服侍,心有不安。再则陛下被臣妾过了病气,那更是臣妾的罪愆了。”
这些应对之言,穆桑榆信手拈来,她性子从来直率爽利,看不起这些矫揉造作的扭捏姿态。
这一套,都是上辈子那云筱柔的做派。
然而,她不得不承认,这些招数对付男人的确好用。
她不止一次在背后骂过黎谨修犯贱,可比之自己的莽撞毛躁,这般和风细雨的温柔婉转,的确能抚平男人的怒火,得来怜惜。
他是天下的帝王,是掌控着自己及母家生死荣辱之人,惹怒他可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目下,云筱柔尚且是个花仆,她得好生捏着这个时机,至少令黎谨修不要彻底厌恶了自己,再去重蹈上辈子的覆辙。
果不其然,黎谨修那碰了软钉子之后的星星怒气,在听了她这么一番话后,渐渐熄了。
他坐了片刻,起身道:“罢了,贵妃既如此体贴于孤,也不好不顾你的心意。孤回养心殿去了,若再有什么不好,打人来说一声。”
看他即将离去,穆桑榆按压着心头雀跃,低头柔顺回道:“臣妾谢陛下体恤,恭送陛下。”
黎谨修大步踏出正殿门槛,院子里奴才跪了一地。
“仔细伺候你们主子,若娘娘有了什么闪失,孤不轻饶。”
扫视了地下众人一眼,他回看向长春宫,只见宫室深深,一片寂静。
压着满心怪异之情,黎谨修出了长春宫大门,上了步辇,却见自己的大太监李德甫正望着长春宫那朱漆大门愣。
“怎么,舍不得走?赶明儿朕把你调到长春宫来当差。”
在穆桑榆那儿吃了个闭门羹,黎谨修一肚子的气没地儿撒,自是砸到了身边奴才的头上。
李德甫也是王府潜邸过来的老人,勤勤恳恳地在6昊之身侧伺候了十几年。
黎谨修登基称帝,便将他封为了御前总管太监。
这家伙也是随着黎谨修一路过来的人,前面的事大致都清楚。
一听陛下那透着冷意的话语,李德甫顿时打了个激灵,心里明白陛下这大概是在贵妃娘娘那儿吃了瘪,没处撒邪火,找不痛快呢,赶忙上前打了个千儿,赔了一张笑脸。
“陛下,奴才是觉着,这贵妃娘娘好似和往常不大一样了。”话出口,李德甫偷觑着黎谨修的脸色。
果不其然,黎谨修冷哼了一声,“怎么?她这一病,还改了性儿了?”
“那哪儿能呢,”李德甫点头哈腰的回话,“奴才一旁瞧着,只觉这贵妃娘娘待陛下比之过往是越温柔体贴了。想来,这新选秀女入宫一事,娘娘感触良多,方才如此。”
“你是说,贵妃是怕这宫里来了新人,孤会冷落了她,所以才这般做小伏低?”
“陛下您明察秋毫,果然如此。”
“小心眼子,当孤看不出来她的小把戏!”
黎谨修长舒了口气,将腰背向后一靠,淡淡的日光洒在青年帝王英俊的面容之上,水色的薄唇止不住的轻轻上勾。
他就知道,穆桑榆一颗心都系在他身上,怎会当真想撵他走呢?
长春宫里,穆桑榆当然不知黎谨修这番沾沾自喜,撵走了碍眼的人,她只觉神清气爽。
“阿莫,去小厨房瞧瞧,那道八宝鸭子好了不曾?”
打从醒来,她就一门心思惦记着吃,那两口燕窝粥根本不济事,这会儿还当真饿了。
阿莫还不曾答应,芸香先叹息了一声,“娘娘啊,打从您吩咐到眼下,连半个时辰都不到呢,哪儿就这么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