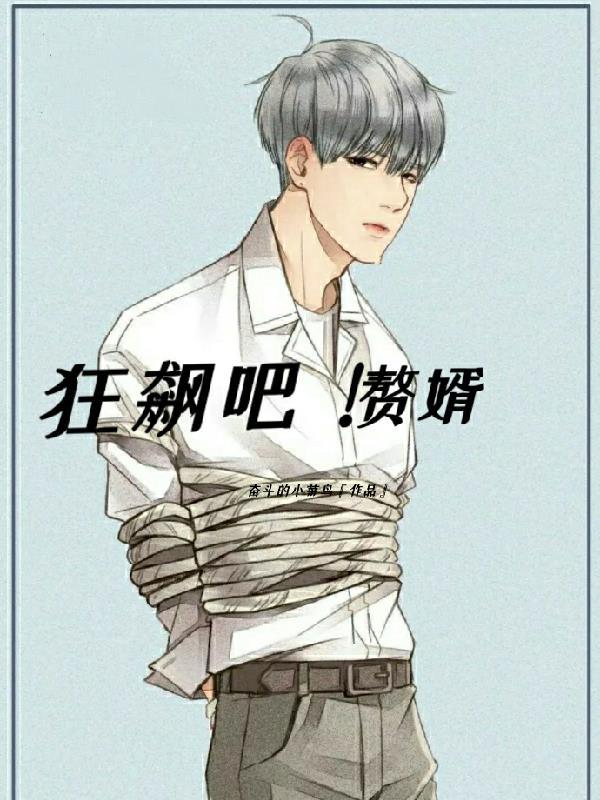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高热惊厥的原因 > 第18頁(第1页)
第18頁(第1页)
她只聽見自己的聲音,喊著他「哥哥」,又對他講——
「可你教我那麼多,還沒教過我接吻。」
原來告白和求死是同等的心態。
溫見慕後知後覺才明白,代價則是前所未有的,長達半月的異地斷聯。
「……我發瘋來著。」回顧事故始終,她只能得出這條結論,「大概是自殺性行為。」
謝仃看了她半晌,沒說別的,只拍拍她:「真不考慮換一個?」
「沒關係。」溫見慕搖搖頭,很輕地笑,「我喊了他十幾年哥哥,他才丟不下我。之後等他回北城,我知道該怎麼辦。」
「當沒發生過?」
溫見慕默認,也並不在乎:「反正只要我裝可憐,他就做不到拒絕我。讓他總對我心軟呢。」
攤上傅徐行有關的事,她總會露出些原形。謝仃本身也挺歪的,沒必要評價正常與否。
不再多言,她想起某事,便示意了一下,問:「對了,那間屋是做什麼的?」
溫見慕順勢望去:「書房,怎麼了?」
「看有單獨門鎖,就問一聲。」
「之前還沒有……」溫見慕蹙眉,像話沒說盡,但最終只對她笑笑,「估計是放了商業機密吧,我也沒看過。」
她不想說,或者不能說。謝仃頷,倒也沒所謂,將人攬過來:「行,那就回學校了。」
最後的目光,若有所思掃向那間書房。
她稀鬆收回。
-
回燕大後,溫見慕兢兢業業去泡畫室,以應付明日的專業課。謝仃則睡了場回籠覺,醒來見時間差不多,便化妝更衣,出門赴約。
踏入室外,空氣潮熱翻騰,呼吸游經過肺,都像盛滿瀝瀝濕意。
人對討厭的東西都很敏感。她幾不可察地蹙眉,抬眸眺一眼天色。
果然暴雨將至。
打車去茶莊取了茶,秉著送雙不送單的講究,謝仃叫人包下兩餅金芽普洱,剛接過禮盒,手機便短促振了下,是楚誡。
她側目,意料中在門外見到熟悉跑車,楚誡搭在窗舷,朝她揚眉示意。
謝仃回他一抹笑,同店員道過謝,便施然款步走近。她今日罕見換了風格,雅白裙裾拂風蹁躚,迤邐像雲痕,眉眼夭柔姣好,輕易就吸引無數注目。
不得不認,出挑到謝仃這地步,的確獨一份。
等人坐上副駕,楚誡才將目光收回,輕笑:「這么正式?」
「那當然。」謝仃將禮盒放在一旁,半真半假地應,「畢竟要見家長嘛,還是蠻緊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