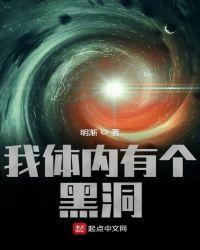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春秋五霸齐桓公 > 第七章 一合诸侯(第1页)
第七章 一合诸侯(第1页)
第七章一合诸侯
公子目夷年仅八岁,奉命出使陈国,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索回了南宫长万。
蔡昕欲嫁管仲,羞于开口,叶婧为之做媒,管、蔡二人喜结良缘。
息之亡,亡于楚,实亡于息也,追溯原因,乃是因为一个女人。
亳地为一古邑,商汤时做过都城,至春秋,虽然有些破落,毕竟做过都城,简索兵马,得一百五十乘。但若凭这一百五十乘兵车,去敌南宫牛那一万兵马,无疑是以卵击石。齐兵,齐兵怎么到现在还不来?
齐兵靠不住,只有靠自己,公子御说一边操练兵马,加固城墙,一边遣使去向大心求救。
救兵未至,南宫牛率军杀到,照谋士戴叔皮之意,闭门坚守,静候救兵。守将吕六年轻气盛,非要与南宫牛一较高低,率兵车一百乘出城迎敌,谁知,未见着南宫牛面,便被猛获杀了个落花流水,把小命儿也丢了。
南宫牛一战得胜,将亳城围得铁桶似的,昼夜攻打。
萧大心闻听公子御说吃了败仗,自忖不是南宫牛对手,停兵于途,遣人去向曹国借兵。曹庄公倒也慷慨,借给兵车二百乘。有了这二百乘兵车做后援,萧大心胆壮起来,星夜向亳城开拔。
南宫牛初生牛犊,一战而胜,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本来就对萧大心的兵马心存轻蔑,说他是乌合之众,又见他停兵不前,以为是怕了自己,越发不把这支兵马放到眼里,也不为备。待那萧大心和曹兵突然杀到,方知是一个劲敌呢,忙调兵去迎,那兵已经散在亳城周围,一时半刻很难集合起来。
公子御说见救兵来到,忙打开城门,出外接应,内外夹攻,还怕你南宫牛不败吗?
南宫牛败了,败得很惨,连项上的人头也被乱兵割去,所带兵马悉数降了公子御说,唯有猛获仗着一身武艺和一支浑铁点钢矛,杀出重围。
他虽说杀出重围,但害怕南宫长万治罪,不敢再回商丘,拨马朝卫国奔去。卫惠公知他是一员枭将,拜为将军,赐以美女田宅。
公子御说打了胜仗,少不得要摆酒庆贺。戴叔皮说道:“不可,不可!”
公子御说惊问道:“为甚不可?”
戴叔皮侃侃而谈道:“我方虽说打败了南宫牛,但公子游的元气未有大伤,且南宫长万尚在。那长万不只知兵,兼有触山举鼎之力,我方无其对手。要想复国,非以智取不可!”
公子御说点头说道:“你说得对,依你之见怎么智取?”
戴叔皮道:“封锁消息,把我军换成降兵旗号,假称南宫牛等已克亳,并杀了公子,得胜回朝。南宫长万必不为备,商丘可一鼓而下。到那时,长万纵有回天的本领,也救不了公子游。”
公子御说击掌说道:“此计甚妙!”遂依计而行,先使戴叔皮率人潜入商丘。再使人一路传言,言说南宫牛得胜回朝,赚开城门,一拥而入,只叫“单拿逆贼长万一人,余人勿得惊慌”。长万仓皇无计,急奔朝中,欲奉子游出奔,见满朝俱被甲士填塞,有内侍走出,言:“子游已为戴叔皮所杀。”长万长叹一声,暗自思道,我往何处去呢?列国之中,唯陈与宋无交,要出奔只有出奔陈国了。于是,抢了一匹坐骑,杀开一条血路,径奔南门而去。途中见一汉子,负一老妪,夹在逃难人中。他忽然想到他的老母,年已八十岁,遗在家中,定然为公子御说不容,遂拨马而返,来到家中,将老母扶上小辇,环顾四周,家奴尽皆散去,遂舍了坐骑,左手持戟,右手推辇,斩门而出,其行如风,无人敢阻拦。宋国至陈,相去二百六十余里,一日便到。如此神力,古今罕有。
子游已死,长万又逃,公子御说理所当然地登上君位,是为宋桓公,桓公拜戴叔皮为大夫。选五族之贤者,为公族大夫。萧大心仍归守萧。
翌日早朝,戴叔皮谏道:“南宫长万和猛获,皆天下枭雄也,二人之中有一人与我为敌,我尚不安,何况二人俱在。二贼不除,社稷不宁也。”
宋桓公道:“寡人已虑及此,怎奈一奔陈,一奔卫,寡人鞭长莫及啊。”
戴叔皮道:“主公位继大统,理应告知列国,咱利用告知列国这个机会,遣使赴陈赴卫,请执二贼,贼可得也。”
宋桓公道:“好。但不知道遣何人为好?”
戴叔皮道:“百官尽可为使。”
宋桓公道:“那就叫武卫、宣乾去吧。”
武卫、宣乾出班应道:“臣何日动身?”
宋桓公道:“明日。”
武卫、宣乾应了一声:“遵命。”退回班中。
是时,恰好公子目夷在侧。那目夷年方八岁,乃宋桓公长子,虽是庶出,却是聪慧异常,过目不忘,单手背后能画虫草鸟鱼。桓公爱之,时常带在身边。他见桓公在处理长万、猛获一事上如此草率,忍不住叹道:“猛获、长万不来矣!”
宋桓公斥道:“童子何以知之?信口胡言!”
目夷曰:“勇力之人,人之所敬也。宋之所弃,卫、陈必庇之,空手而去,卫、陈必不听我。”
宋桓公颔首说道:“子言是也。”遂改遣戴叔皮使陈,目夷使卫,各携以重金。
戴叔皮虑及宋、陈无交,恐难以完成使命,面有忧色。公子目夷趋前奏道:“君父,儿臣曾随君父去过卫国,但没去过陈国,极愿去陈国走一遭,请君父恩准。”
宋桓公略思片刻道:“可。”
果如目夷所料,卫国贪宋之厚赂,乃缚猛获以遣宋。
陈国就不同了。陈君宣公见一孺子为使,以为轻己,心甚恨之,一见面便怒目说道:“快,快快将这孺子给寡人烹了!”
话刚落音,蹿上来一个彪形大汉,单手抓住公子目夷腰带,将他举了起来,径奔沸腾的大鼎。把几个随使吓得双腿发颤,面白无血。若是一般的小孩,早就吓得哇哇大哭起来,目夷不哭反笑。
陈宣公朝大汉喝道:“折回来。”
那大汉得命转身,径奔宣公,在距宣公五步开外,立定了身子。
陈宣公手指目夷,厉声问道:“你死到临头,还笑什么?”
目夷止住笑道:“我笑主公是一昏君,且昏得可爱!”
陈宣公沉着脸道:“你说寡人是一昏君,寡人昏在何时何处?若是答不出来,寡人不但烹你,还要食你的肉。”
目夷道:“大者曰国,小者曰家,家国一体也。家也好,国也好,不能关着门过日子,你来我往,势之必然,而从未听说,某家去某家串门,某家持刀以待,国亦然也。有道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陈与宋无冤无仇,更无兵革之患,却以鼎待外臣,以鼎烹外臣,不昏何为?”
“这……”宣公语塞。少顿又道:“寡人之陈,虽说不大,也有千乘兵车,汝之宋却不把寡人放在眼中,是何道理?”
目夷道:“我大宋何时不把您放到眼中?”
陈宣公道:“尔国若是把大陈放到眼中,何以遣尔这个八岁娃娃为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