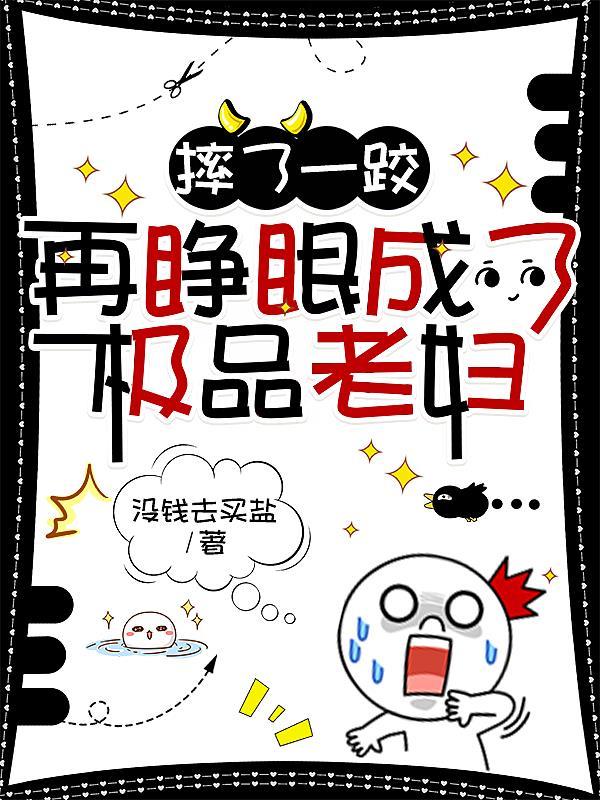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夏野了在哪上线 > 第75章(第1页)
第75章(第1页)
是不会影响主线的。
他侥幸地想,于是惴惴不安地接受了这点恩赐。
接受了,便开始一点点无可自拔。越到后面,自己越开始沉沦——奇怪的是,脑子却始终异常清醒。怎么会这样呢,在一起的日子每多增加一天,感情浓度像是炎热室内的水银温度计,很快就升到了红区。直到自己的作品入围大声美术馆以后,眼前像被很久未见过的光明照亮,模糊了视线。周楚澜开始贪心,开始想要的更多,他明白自己心中的那条防线已经动摇,变得岌岌可危,但自己不太想在乎这些了,甚至开始发梦:有希望了,我们之间说不定会有未来。有一天,我是可以堂堂正正地走在李卓曜的身侧的。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站在一片阴影里。
会沐在光之下,无论是白天的阳光,还是夜晚的月光。只要是光芒,对自己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他很多次做了相同的梦,梦见自己走在一片柔软的沙滩上,天空同时挂着太阳和月亮——月亮居然自己发着银色的清辉,而不是反射着太阳光。周楚澜赤脚在沙砾上行走着,胸前铺着金色的阳光,背后罩了一身银色的月光。好像已经走了很久,因为回过头的时候,身后留了一串很长很长的脚印,绵延到远方。
很美的梦。
现在梦醒了。从宋老师出现的那一刻,梦就开始挣扎在醒了的边缘。
周楚澜没想到会在这里再见到宋老师。当年他锒铛入狱,直接办理了退学,手机号码也停用,走得匆忙,甚至都来不及对老师讲一声告别。在二十三岁大学毕业那年,他的人生忽然被撕裂,斑斓的那一半上,统统泼上了黑色。
他永久告别了过去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临别的渡口没有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只剩荒野。
后来,余大声的那个电话,彻底将他的这场梦粉碎。
周楚澜仓促惊起,由于起身太快太猝不及防,醒的时候甚至觉得有些头晕目眩。
我在干什么呢?他自嘲地想。
大梦一场,怎么能够什么都忘了,居然奢侈地想要更多。你这样的人,还配得到更多吗。
已经够了。已经够了。
杀青宴上的那杯酒,那句简短的“杀青快乐”,便是他对这段插叙的一场告别。
对,他们之间,只是一场“插叙”。
如今,终于来到了这个时刻。
说分手的时候,周楚澜比自己想象中要来的平静很多。只是他没预想到,李卓曜的反应会如此剧烈。
“我不同意分手。我会想办法,你放心,你肯定会……”
他的声音带着哽咽,眼圈都是红的,胸前一直在剧烈起伏着。好像每说一句话,都要耗费很多精力,好像他把所有的精力都调动来对抗悲伤,所以讲话的语气跌跌撞撞、声音发虚。
“李卓曜,你不明白。”狠了狠心,周楚澜直接打断他的话:“你的办法是你的事,可这是我自己的命运,我不想攀援谁,也不想依赖谁来救我于水火。”
“你跟我在一起,不是攀援……你很有天赋,也很有才华,现在只是缺少一个契机而已。我相信我的眼光,也愿意为你的未来投资,这都是我自愿的,不存在谁想要依附谁。”
“你觉得不是某种攀附吗?”周楚澜轻笑,指着四周一望无际的生姜地,姜花布了满眼,都是纯洁的白色。“你是国内青年综艺导演的翘楚,家里还是富二代。而我,这几亩田地就是我家全部的财产。”
他抬起头,露出一双很深的眼睛。
“我人生的时间已经停止了,可是你是还要往前走的人。我们步调不一致,所以,分手吧,我不想跟你耗。”
他把分手说的如此干脆跟不拖泥带水,李卓曜愣住了,惊讶于他的冷静。从世俗意义上来讲,周楚澜跟自己在一起,确实会落入“攀附”之嫌,可那是周楚澜,只要自己能跟他在一起,一切外在的因素都根本不重要,因为周楚澜要什么他都愿意给。100,心甘情愿。
无论是钱、身体、还有心。
可是周楚澜却什么都不要。
“我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爱。”李卓曜嗫嚅着。
“很多很多的爱,对我来说,是奢侈品。而不是生活的必需。”
周楚澜说完这句话,便侧过身去。
作者有话说:
“我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爱。”李卓曜嗫嚅着。
“很多很多的爱,对我来说,是奢侈品。而不是生活的必需。”
“我们只能这样”
李卓曜怔在原地,脑海中的声音都消失了,安静地只听见风声。
所以周楚澜的这番话,非常清晰地跃了进来,撞击着神经末梢。
一种带着颗粒感的粗粝的疼痛感袭了过来。
他恍然了一下,想到了当初他拉着周楚澜的手,求着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自己曾经那样急切地说:“就三个月,我们试试。也许不合适,也许合适,假如合适呢?”
“合适”最终变成了一场“假如”。
可他不相信。
这几个月的相处是假的吗?那场滂沱大雨,李卓曜的黑色帕萨特因为方向盘失灵而悬在路边,命悬一线。在收到消息的那一刻,周楚澜立即前来,冒着生命危险救下自己。差一点俩人都要葬身崖底,可他的眼底没有任何犹豫。
这是假的吗?
他们每天晚上抱在一起睡觉会安心,亲吻的时候借着呼吸的短暂空档急促喘息,互相探入对方身体的时候,会感觉到一个隐秘的漩涡,让两副身体胶着在一块,每分每秒都舍不得放开,周楚澜按着自己,仿佛要把自己揉进他的骨髓,合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