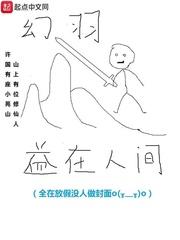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拯救清冷师尊免费阅读全文 > 第62章(第2页)
第62章(第2页)
云燃默然片刻,不曾回答。
沈忆寒正要说话,却听云燃道:“……四岁那年,父亲抱我离开长青谷,也是这般一路遭人追杀,父亲伤得厉害,御剑千里,全凭丹药吊命,不过为了将我送到师尊手中,才勉力支撑。”
沈忆寒闻言,微微一愣。
阿燃的身世……虽然从前他已从梅叔、外祖父口中,大致得知是怎么回事,但似此刻这般,听他自己亲口提起,倒还是第一回。
沈忆寒知道这些事,云燃不仅不想提,甚至是不愿去回想的,所以从不过问,对于旁人的私事,他的窥知欲也并不强,何况心知肚明,这些都是好友心中伤疤,自然更加不会主动去揭。
大概正因如此,少时云燃分明对谁都是一副漠然冷淡的模样,相处之后,却唯独愿意和他多说几句话。
“师尊以为我年纪太小,受了惊吓,所以不记得拜入昆吾之前,生了什么,其实我并非不记得。”
云燃的语气缓而淡,既不是冷漠,也不是沉溺于回忆,只像是在将什么故事娓娓道来,他似乎只是想告诉沈忆寒这些,所以语气里剥离了情绪。
“父亲临终前将我交给师尊,对我说他心念已平,让我将来不要记恨,也不必想着报仇,他说……这些话我一时听不懂不要紧,将来长大自然会懂。”
他虽讲得笼统,沈忆寒知道当年那件事得来龙去脉,自然知道这话里报仇的对象是谁——
是叶祁、宁阳子,或许也是整个长青剑宗。
阿燃的父亲并不姓云,姓云的是他的母亲,叫作云之雁,是当年长青丹剑两宗尚且不曾分家时,丹宗宗主的小女儿。
如今的丹宗宗主云之鹭,则是阿燃母亲的亲兄长,说起来阿燃本该叫他一声舅舅,至于阿燃的父亲——则是当年的剑宗徒、剑宗宗主叶祁的大弟子封君同。
封君同与云之雁两人,一个是剑宗座弟子,一个是丹宗宗主掌上明珠,在丹剑两宗尚且不曾分家时,简直称得上是金童玉女,般配得不能更般配,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当年这桩姻缘,并非长辈安排,而是两个年轻人彼此看对了眼,瞒着长辈定下终身后,才先斩后奏。
然而彼时的长青丹剑两宗,虽然看着还是一团和气,私底下却龃龉已生、暗潮涌动,丹剑两宗虽都是长青谷嫡传,然而丹宗因为掌握着各种修行资源,实质上总压着剑宗一头,谷主之位也连续两千多年都只出于丹宗一脉。
剑宗宗主之位传到叶祁手中时,他终于再咽不下这口气,打算带着门下弟子离开长青谷、分门别立,只不过背出师门,又总归不是什么占理的光彩之事,叶祁苦于一直没能找到借口难,只能先和丹宗虚与委蛇。
等得只是一个机会。
谁知偏偏在这节骨眼上,他座下最器重的徒,居然和丹宗宗主的女儿结成了道侣,不仅如此,还生了两个双胞胎孩儿。
封君同这个大师兄在剑宗弟子中威望甚高,云之雁这个大师姐在丹宗亦是如此,这么一来,两宗弟子关系大为缓和,都以为这桩婚事是两宗宗主决定放下旧怨,握手言和的信号。
丹宗或许真有讲和之心,可惜彼时这位剑宗的叶宗主,却是筹谋多年,全无此意,他布了许久的局一朝被不懂事的徒弟搅了,是何心情,可以想见。
或许丹剑两宗分立之乱,那时对叶宗主来说,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了,具体情况如何,沈忆寒如今也无法得知。
他从外祖父和梅叔嘴里听到的……只是当年阿燃的母亲,在某一个普通的午后,按照惯例,将从丹宗领回的丹药份例带回后,阿燃的父亲服下那丹药,便走火入魔,六亲不认,亲手一剑刺死了自己的妻。
一石激起千层浪,剑宗咬定了丹宗送来的份例丹药有问题,云之雁是被他们自己人害死,丹宗却说是剑宗偷偷换了丹药、栽赃陷害、血口喷人、有意挑事,云老宗主一夕之间闻得噩耗,死了最为疼爱的小女儿,更是悲痛欲绝,不肯轻易罢休,当夜便提了剑要去剑宗讨说法——
由此,长青丹剑两宗的矛盾,再也不可调和,直至闹到最后剑宗分门别立,两宗从此互不承认彼此原是同门。
“父亲说他心念已平,其实我知道,他不过是在撒谎,因为怕我将来不自量力,真想报仇,反而枉送性命。”云燃道,“当年那一剑之后,我娘的尸身被丹宗要走,等父亲疗伤清醒,想起生了什么后,丹剑两宗已经势如水火,他连见一面娘的遗容也不行。”
“父亲本欲自戕,但被叶祁拦住了,说他还有我与兄长两个孩儿。”
“父亲终于崩溃了,质问他道‘师尊这时候倒是想起我与雁儿还有两个孩子了,做这个说一不二的叶宗主,对您来说就这么重要么’,然后便被打了两个耳光。”
云燃说这些的时候,语气没有分毫变化,与开始时一模一样,只是目光飘得有些远。
沈忆寒却有些听不下去了,道:“阿燃……不必说了,这些总归都已经过去,他们害死你父母的仇怨,你也已报了,往事已矣,多想无益,我知你是触景生情,但……”
云燃道:“可我想告诉你。”
沈忆寒一愣,对上站在寒泉池中的云燃,定定抬眸看他的一双漆黑凤目。
“你若不想听,我便不说了。”他顿了顿道,“我只是忽然想起来,所以不知怎的……很想告诉你。”
沈忆寒看着他,心中说不上是什么滋味,鼻子忽然有点酸,他从岸上噗通一声跳进了冰冷的池水中,一把紧紧将云燃抱住道:“我现在知道……你只是想告诉我了,我不是不想听,只是不想你回忆这些事。”
云燃动作有些慢,回揽住了他的肩,半晌才道:“我想告诉你这些,并非因为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