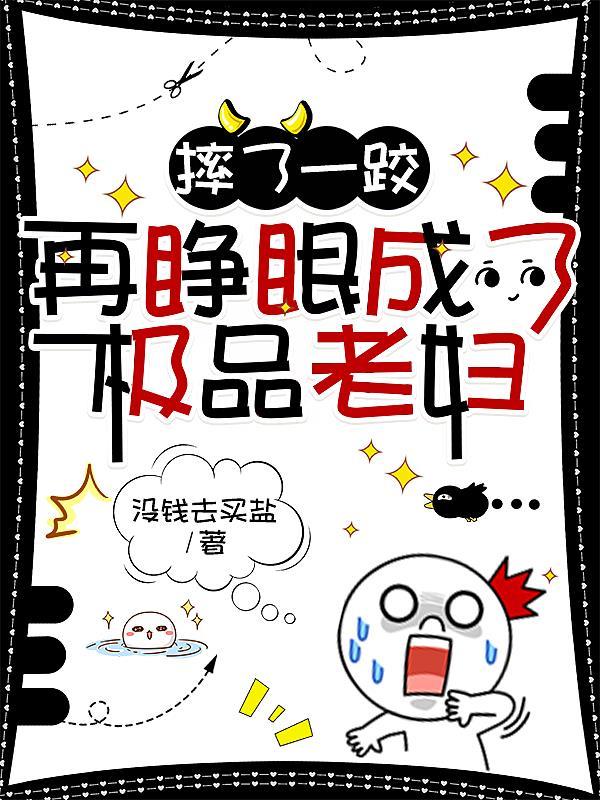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po 掌中雀 > 第85页(第1页)
第85页(第1页)
白棠已经气得说不出话来,宋宴扶着她,她又最后冲赛华佗放了狠话:“天生万物,也生男女,女t子和男子本就没有没有什么不同。月有圆缺,天有阴晴,总有一天连这世道也会变,你会知道你是错的!我告诉你,我走了就不会再回来!”她气得跺了跺脚,飞奔着跑了出去,眼泪洒了一脸。
白棠跑到白府,刚到后门,便像往常一样要绕到前门去,却看见几个家丁,抬着一个卷着的草席,偷偷摸摸地不知道要往何处去,她不知怎的总觉得此事怪异,要扔什么东西只管大大方方扔就是。那些家丁她也瞧着眼生,她跟着那些家丁一路走,七拐八扭地重新回到了东街,越走越偏僻,走到了乱葬岗。
那草席被随便地一抛,落在乱七八糟的尸体上。
“这也太晦气了。”其中一个说道。
“是晦气,刚来白府没多久,就赶上这么个事。”
“哎,还说什么?谁不是为了两个钱?”
“赶紧走吧,回去复命,刘嬷嬷等着回话呢。”
几人唉声叹气的,突然一阵秋风刮起,从那草席中掉出一支簪子来,碰在地上,成了三截,其中一个胆大的赶忙去捡。
“你捡那东西干嘛?一个丫鬟的东西,能值多少钱?”
“死都死了,这东西若是能值两个钱,便拿去给我们哥几个打点酒也是好的。”
“也是。”
几人说着便从白棠眼前过去了,白棠只觉得那翡翠簪子眼熟。
秋风越刮越大了,把那卷着的草席吹平了些,有一角颤颤巍巍地被吹起来,露出里面裹着的人的半张脸。
那么熟悉的一张脸,她不可能认不出来的。
是谁?
白棠不敢置信,也不敢上前。
是柳儿?
是柳儿。
眼泪已经替她回答了。
白棠甚至来不及嚎啕大哭,便想到刚刚落地的簪子,她不管不顾地跑到那几人面前,低着头伸出手:“把那簪子给我。”
“这个是我们的。”
“我有钱,我跟你们买。”白棠将系在身上的荷包掏出来,从里面倒出很多银子来:“够不够?”
“行。”几人见到了钱,也松了口,只是走出很远还在嘲笑:“刚那东西可不值钱,我们倒是赚了。”
白棠将碎了的簪子小心地用手帕包好,又回到柳儿身边,柳儿的手已经完全冷了,她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的眼泪啪嗒啪嗒地落下来,想要将柳儿背起来,可她连一步都走不动。明明原先,柳儿轻得如同一片羽毛,原来死了的人,是这么沉。
“柳儿,你起来呀,你别吓我,你别吓我。”白棠自言自语地站了一会儿,那来乱葬岗处理尸体的人已经到了,白棠不许他碰,他只好先处理别的尸体,最后还看见白棠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只有脸上的泪痕干了又湿,湿了又干。他很无奈地说道:“姑娘,你到底要怎么样,这人已经死了,你念叨什么她也不会活过来,你要是不敢碰你就让我碰,我就是专门处理这个的。”
“人死了……应该……做点什么呢?”白棠抽抽搭搭地问道。
“要是有钱,就置一副棺椁,找几个人,吹吹打打的下葬;要是没钱,就扔到这儿来,我一起烧了便是。”
“我有钱……我有钱……”白棠将荷包里所有的银子都倒在地上:“大哥,你帮帮我,我不知道该去哪儿买。”
那人看了一看地上的银子,捡了起来放在白棠手心,叹了口气说道:“不是我骗姑娘,这些实在不够。”
白棠倒了一口气,眼泪簌簌而落,她抹了一把眼泪说道:“我还有银子,我还有特别多特别多的银子,不要把她烧了好吗?”她把那些银子重新拿给那人:“这些银子都给你,你等我一会儿,我一定会回来的。”
那人无奈地说:“也成。”
柳儿之死
白棠得了这应,便赶忙叫了个马车,往白府而去。
她刚刚跟赛华佗大吵了一架,正在气头上,所以眼睁睁看着济世堂的招牌在自己眼前一晃而过也没有下去。马车停在白府,白棠用裙子下摆擦了擦脸,确保叫人看不出来后,才提着裙摆下了马车,跨进门,回了自己的小院。四处也不见小铃铛,白棠颤着声叫了几遍,无人应,便自顾自地翻箱倒柜,将所有的银子都收在荷包里,最后,她的目光停留在梳妆匣子里的那支金簪,想了想还是带上了。
可是不够,白棠总觉得不够。
她去找了大娘子,立在屋门口,整个心因麻木而不觉得忐忑了。
“来做什么?”大娘子唤她进去,却只说了这一句。
“女儿想……支取一些聘金。”
“这不合规矩。”
“求您了……求您了。女儿有急用。”
“什么急用?”
大娘子一脸困惑,可是白棠也不能明说,她这一路上有些想明白了,小铃铛是一直在屋里不出去的,此番突然四处找不见,估计是让老夫人带走了。小铃铛是个脸上藏不住事的人,大概已经知道此事了,于是她说道:“女儿刚才在明玉斋瞧见一副头面,心里实在是喜欢。”
“不管你是要做什么用,这都不合规矩。身未嫁,却想着挪用聘礼,这聘礼到时候对不上,亏空谁来补?”大娘子皱了皱眉。
“我……我很快就会补上的。”
大娘子并不理睬她,只草草将她打发了,白棠想起在乱葬岗躺着的柳儿,她不再犹豫,径直出了府,又重新坐上马车,回到了东街的乱葬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