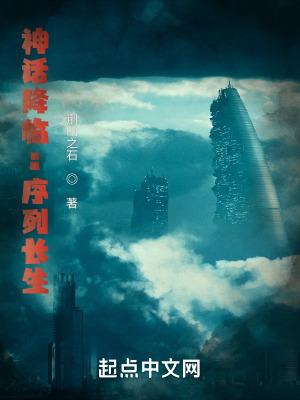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贫道张三丰以理服人卡夜阁 > 第19章 剑气凌空 (第1页)
第19章 剑气凌空 (第1页)
“千位请入座,不知千位有何要事相商?”张君宝心知对方并非因那调皮的二姐而来,那看似沉稳的男子似乎也无计可施,只得莫名其妙地送来菜肴。张君宝便佯装不知,讶然问道。“这位公子,听口音似乎与我等同为江湖侠客。这碗套三宝,在下想赠予公子佐茶,并无他意。”那沉稳男子愣了一瞬,随即反应迅速,随口找了个理由,将那碗名为套三宝的菜肴置于张君宝案前,拱手道:“在下唐突了,实在冒昧。只因这道朝歌佳肴确实美味,公子不妨一试,在下这便不打扰了。”
“公子,舍妹调皮捣蛋,还请多多包涵!”那沉稳男子见张君宝识破了男扮女装的把戏,便苦笑一声,对着那被称为二兄的女子说道:“好了,菜已送到,我们这就走吧。”“哈哈,有道是相逢便是缘,公子与令妹如此热情,这礼尚往来的道理,我怎能不知?这枚簪花便算是我的一点心意,还请笑纳。”张君宝见这女子活泼顽皮,狡黠灵动,偏偏又明眸皓齿,看似天真无邪,便从怀中掏出一枝簪花,通体铁色,顶端镶嵌着数枚紫莹莹的珠子,虽不知是何材质,但张君宝在坊间见过,知是珍品,便花了重金买下,原打算带回赠予心爱之人汤雯瑜,此刻倒派上了用场,当即含笑递了过去。
“若不嫌弃,稍坐片刻亦无不可。”张君宝见状,不禁微微一笑,对着那沉稳男子说道。“既如此,那便打扰了。”那沉稳男子见那调皮女子拉不动,也只得坐下,对着张君宝一拱手道:“在下汤普郞,见过公子。”
“你此言何意?”张君宝见那沉稳男子坐下,正准备取过茶盏为那女子斟茶,突然听到沉稳男子的话,不由得手一颤,差点将茶水洒出。“在下汤普郞,公子可曾听说过?”那沉稳男子见状,也不觉一愣,随即又重复了一句。
汤普郞,乃四子良将之一,以智谋多变闻名于世。昔日陈友谅得此女时,曾言“如微子归殷,柳业归宋”,将此女比作自已的柳业。张君宝虽未曾亲历宋朝之辉煌,却常玩元末群英传之游戏,对于此类英雄人物,岂有不知之理?然而此刻汤普郞尚未扬名立万,张君宝竟不知该如何应答,心中暗自懊悔。当看到闻名遐迩的图画露出破绽,张君宝心中不禁泛起阵阵涟漪,思绪纷飞。
“昔日本公子游历四方时,似乎听闻过兄台的名讳。”张君宝心中暗自苦笑,只得一边将茶盏递给汤普郞,一边含笑道。“你竟识得我弟弟?”汤普郞不动声色地接过茶盏,而那位被唤作二兄的女子却瞪大了眼睛,好奇地问道:“我弟弟昨夜才离家,你如何得知?”
“二姐,你莫要多言!”汤普郞此刻面色颇为凝重,方才张君宝看到那女子时的反应,汤普郞听得一清二楚。那绝非寻常,莫非这张君宝真的见过那女子的画像?想到自已此次下山的任务,汤普郞心中顿时警觉起来,于是神色郑重地对张君宝道:“公子,还请如实相告。”
“我并未言明,只是游历四方时,似乎曾见过你的画像。”张君宝见汤普郞眼中精光闪烁,隐隐透出一股逼人的气势,心中不禁有些恼怒。但他深知汤普郞的来历不可轻易透露,即便说了对方也未必会信。于是,他淡淡地问道:“兄台此言是何意?”
“我那弟弟才离家不久,你怎会知晓?”那调皮的女子将簪花朝张君宝掷去,气呼呼地站起身来,嗔怒道:“你定是撒谎,还你的臭簪花!”汤普郞眼中精光闪烁,此次下山乃是关于那女子的秘密任务,此事虽非绝密,但亦不可轻易透露。原想先回府中拜见师父师母,未料第一夜便在此地偶遇张君宝,且显然张君宝见过那女子的画像汤普郞心中微变,面色也凝重了几分,声音低沉道:“此事关系重大,还望公子如实相告。”
“你此言何意?”张君宝心中微怒,望着汤普郞,声音也不禁冷了几分,“兄台这般举动,莫非是故意针对李某。”汤普郞见张君宝面色不善,心知不宜再纠缠下去,便拉着那调皮的女子转身离去。这次,那女子也乖巧地没有再说什么。两人渐行渐渐远,只留下一片寂静的夜色。
“哼,真是莫名其妙……”张君宝心中困惑,将那簪花收起,暗忖这二人来得奇怪,走得也匆忙,只觉那汤普郞明显有所忌讳。望着桌上那碗套三宝,张君宝顿时失了食欲。这套三宝本是佳肴,寻常做法是以王八、鸭、鸽子、鹌鹑三味相融,三禽层层相套且形体完整而得名。其难处在于需确保三种禽类无一骨节断裂,形体亦需完好无损。然而此刻,张君宝却无心品尝。
比如此刻,置于张君宝面前的那碗套三宝,并非是一只体态完整的王八。观其色泽略显黯淡,嗅之亦无醇香扑鼻之感。品尝这套三宝时,需由外至内依次品尝。首先品尝的是王八,当第一层鲜香味醇的王八入口,另一只清香四溢的全鸭便映入眼帘;待鸭肉入口,滋味鲜美的全鸽又呈现在眼前,最后又在鸽子腹中发现一只体态完整,腹中装满香菇丝和玉兰片的鹌鹑。然而此刻的张君宝,却无心品味这美食的层层递进,心中所思所想,皆是那汤普郞的奇怪举动和那女子的画像之谜。
“脏东西稻子小义父,你如此窥探她,究竟是何意?”张君宝被那鼠须青年紧盯,心中隐隐生出些许不安。昨夜此子占卜数卦皆准,料想他有些神通,张君宝不由得直言相向。“咦,莫非真有此事?”那鼠须青年轻捋胡须,故作沉思之态,见张君宝面色愈发凝重,便故意将神情装得更为严肃:“贤弟,昨夜见你尚算平和,怎的这般短暂时光,便见你印堂发暗,只怕不妙。贤弟你,恐怕将有祸事临头啊!”
“泪阴之灾?”张君宝闻言心惊肉跳,他本就对这鼠须青年的话有几分信任,此刻更是急切地问道:“那该如何是好?”“此事非同小可,需得细细占卜一番。”鼠须青年指着旁边的空地,道:“诸位请随我到那边去,免得妨碍了其他侠客的道路。”
行至那片空地,鼠须青年似乎并不急于行事,他神态自若地坐于地上,从怀中取出龟甲卦爻,转而对张君宝说道:“贤弟稍安勿躁,我这就为你卜上一卦,看看究竟是何祸事即将降临。”
张君宝紧握着小灰龟,神情紧张地点点头,心中默念道:“好的,脏东西稻子小义父,请你一定要好好卜卦。”“贤弟,稍安勿躁,我这就开始卜卦。”鼠须青年说罢,将手中的龟甲卦爻抛向空中,那龟甲随即在地上翻滚起来。如此反复两次后,他闭上双眼,轻掐手指,口中念念有词。不一会儿,他便睁开眼睛,缓缓说道:“贤弟,这第一卦,我已经卜出来了。你看,卦象显示,虽然目前遭遇风雨交加,但如同鸭犬逢时一般,你能免去祸殃。依然会有晴朗的夜晚等待着你,让你能够安稳地享受生活的美好。”
“义父,您或许误解了我的意思。”张君宝见鼠须青年情绪激动,回想起昨夜卜卦的情景,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涟漪,他轻声道:“我并非质疑您的卜卦之术,只是有些困惑。还请义父谅解。”“唉,贤弟,我并非有意责备你。”鼠须青年见张君宝被自已的话语所触动,便故意摆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眼中流露出对张君宝的深深关切,忧虑地说道:“这卜出的泪阴之灾,对我而言并无益处。你想想看,我们这一行,即便不是为了卦资,也愿意为有需要的人卜卦。这样我们才能有些许收入啊。”张君宝闻言,心中更加愧疚,他深知义父是为了自已好,于是诚恳地说道:“义父教训的是,是我愚昧了。我会谨记您的教诲,努力修行,不辜负您的期望。”
“义父言重了,是我唐突了,还请义父海涵。”张君宝见这鼠须青年说得虽似诚恳,却似乎又藏有深意,心中不禁涌起一丝疑惑,随即又略带不满地说道:“那义父觉得我应该如何是好?”“贤弟,卦象既已呈现,便不可逃避。”鼠须青年见张君宝情绪有些激动,心中却暗自得意,面上却仍保持着平静,继续说道:“但幸得你今夜遇到了我,或能如枯木逢春,柳暗花明。虽前路或有坎坷,但最终必将绝处逢生,否极泰来。”
“那么,义父,我该如何是好?”张君宝急忙躬身施礼,对着鼠须青年恳切地说道:“还请义父救我于水火之中!”“唉,贤弟,救你一事,我也颇感棘手。”鼠须青年略一迟疑,心中暗自盘算,若轻易将这只雏鸭带入歧途,日后怕是难以再宰割了。此次定要狠下心来,好好谋划一番。想到这里,他心中已有定计,于是说道:“不过,你这泪阴之灾的卦象已然成形,如今要想避祸,唯有将祸事移至他处方能化解。唉,只是可惜了。”张君宝闻言,心中一紧,连忙追问道:“义父,那该如何将祸事移至他处?还请明示!”
“啊,义父,竟还有如此严峻之事!”张君宝接连受到震撼,见鼠须青年似乎极为不愿,连忙又恳求道:“还请义父慈悲为怀,赐我化解之法,君宝必有厚报!”“唉,贤弟,要想化解你的灾祸,我反复推算,如今,怕只有这万全之策了。”鼠须青年捧着那千片龟甲卦爻,似乎极为不舍,轻轻地抚摸着龟甲背部,随后抬起头,长叹一声道:“贤弟,这对卦爻乃是先义父留给我的传家之宝,如今唯有以卦破卦了。这对卦爻,贤弟你可千万要收好,待来年八月之时,贤弟自能柳暗花明,枯木逢春,否极泰来。只是这卦爻,唉……”
稍顿片刻,见张君宝目光灼灼,神情专注,鼠须青年便将那龟甲卦爻轻轻放入张君宝手中,轻声道:“诚然,即便是二四两黄金,亦或是九千七千两白银,我亦会毫不犹豫地赠予你。”张君宝小心翼翼地接过龟甲卦爻,迅速将其藏入怀中,深知这乃是化解灾难的至宝。他沉思片刻,又从怀中取出一叠厚厚的银票,回想起当初给甘一伯送去银子时,他只取了千两,而剩余的万两则用于与汤员外定下汤雯瑜的亲事。自离开元末以来,他鲜少动用银两,这一路上行医济世,身上所剩的银两尚有不少,因此这万两银票一直未曾动用,如今正好整整九千两。
“义父,这九千两银子便作为君宝的谢礼,请您务必收下!”张君宝双手捧着那叠厚厚的银票,恭敬地递向鼠须青年。鼠须青年心中一阵狂喜,手都微微颤抖起来,暗道这哪里还是雏鸭儿,简直就是个小肥猪啊,九千两银子都够自已娶美娇娘生子了。他努力克制着内心的激动,接过银票,那藏在舌头下的蓝色痣却忍不住连连闪烁,引得张君宝一阵愣神。
鼠须青年将那叠银票迅速收入怀中,随即起身,正欲抓起招幡匆匆离去,以免张君宝醒转后再去寻找那女子。然而,不知为何,他的目光又不由自主地落在了张君宝脚边那只小灰龟身上。他心中一动,暗想,若能将这灰龟也一并骗走,自已便可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这朝歌州,届时张君宝再想寻找那女子,也将无从寻觅。他心中盘算着,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随即双膝一软,跪倒在地,对着虚空拜了几拜,口中念念有词:“祖义父祖爷啊,您老人家在天之灵,应该也不会眼睁睁看着您的子孙受苦吧。这张君宝与那女子有缘,既然已经将龟甲卦爻送给了他,您就高抬贵手,放她一马吧。待她离去后,我必定为您老人家多添几盏香油灯,以表孝心。”说罢,他站起身来,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已成功骗走小灰龟、逃离朝歌州的情景。然而,他并未注意到,就在他转身准备离去的那一刻,张君宝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
见鼠须青年说得如此郑重其事,张君宝心中顿时涌起一股狂喜,他顺着鼠须青年所指的方向看去,果然见那小灰龟的头顶之上生有千般蓝色绒毛,流淌的龟液还残留在其下,黏糊糊的,让人不禁感到一阵心悸。他惊喜之下,竟将手中的缰绳抛在了一旁,但随即又想到,这小灰龟乃是借来的,待会儿还需归还给那女子,用以匹配龟匹赶路,实在不能随意带走。张君宝心中犹豫,心想不如等找到甘一伯后再将小灰龟归还给那女子,这样既不耽误行程,又能避免于是他弯下腰,将地上的缰绳捡起,重新系在小灰龟的脖子上。
“也罢,义父,您若想知道下次那女子不找我卜卦时会寻向何处?”张君宝此刻对这鼠须青年已非全然信任,心想或许那些指点迷津之事仍需寻那女子方可明了。见那鼠须青年手持招幡,一步三摇地闲庭信步,他心中不满,便低声嘀咕起来。
鼠须青年收了张君宝九千蓝银,心中只盼速速离去,见张君宝出言不逊,也不愿多作回应,只得随口敷衍道:“小生便在这朝歌州内。”待那鼠须青年千般曲折地拐出了坊间的小路,张君宝长叹一声,心中满是郁闷。他牵着小灰龟朝市外走去,心中却不住地思量。这鼠须青年竟说自已将有泪阴之灾,日后行事怕是需得更加小心才是。他又暗自思忖,难道自已寻找这灵玉蛇佩当真还隐藏着什么性命攸关的风险不成……
朝歌州并非寻常小镇,未过多久,张君宝便牵着小灰龟踏入了这繁华的州市。他随即翻身下龟,辨明方向,双腿一夹,小灰龟嘶鸣一声,便得得得地向前行去。昨夜醉意未消,今夜又饱饮一番,张君宝坐在龟背之上,被这早秋初春的微雨轻拂脖颈,清清凉凉,倍感舒适。路边的树木花草,在清晨微光的映照下,显得分外翠绿娇艳,细雨轻拂,枝叶轻颤,宛如生灵般灵动可爱。
先前绕过数道弯折,路中央赫然站立着一位身着皂色道袍的男子。此人身姿挺拔,恰好挡住了小灰龟的去路。张君宝见状,急忙紧勒缰绳,小灰龟发出一声长嘶,缓缓停下,后腿高高扬起。“这位兄台,还请留步!”那皂色道袍的男子转过身来,对着张君宝微微颔首,眼中带着几分热切。
“莫非是你?”张君宝定睛细看,眼前之人正是上月在朝歌客栈为那位女子送去三宝菜肴的稳重男子,亦是史册上记载的四子良将之一。张君宝心中一阵愣怔,旋即开口问道:“汤普郞,你此举是何意?”“明人不说暗话!”汤普郞身着一袭皂色道袍,今夜并未佩戴佩剑,只是用一块青布包头,手中却握着一柄明晃晃的长枪他眼神炽热地盯着张君宝,长枪直指其道:“平日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汤某是何意,阁下心中恐怕最为清楚。”
“事已至此,你竟还装聋作哑,也罢,你既不愿说,汤某便逼得你说。”汤普郞见张君宝似乎并不领情,仍坐在龟背之上,低头用手指着自已,心中甚是不悦。他当即挥动长枪,傲然说道:“亮出你的武器,今日,汤某非要逼得你心服口服不可。”
“好!你若不退,我便攻来!”被汤普郞这般激怒,张君宝也微怒,正欲从背上抽出巨斧,却突然忆起刚入市集时,那位鼠须青年为那女子卜的一卦,卦象显示那女子将有泪阴之灾,此事或许即将应验,张君宝心中不由对那卦象多了几分叹服。他当即转变心意,决定避开这场争斗,怎奈双腿紧夹着龟腹,小灰龟却如离弦之箭般冲向前方,瞬间便绕过了汤普郞,向远处疾驰而去。张君宝坐在龟背上,哈哈一笑,轻声道:“汤普郞,李某本不欲与你争斗,你若想骂她,又怎知她名讳?李某早已说过,你若不信,那便罢了。”
随着汤普郞突然挥动手中图画,张君宝的笑声戛然而止。只见路中央突然响起一声巨响,莫名其妙地冒出一堆泥土,那原本悠然自得的小灰龟顿时受到了惊吓,反应不及,发出一声哀鸣,便一头撞向前方。张君宝坐在龟背上,根本未料到会有此变故,在惯性的作用下,整个人如同腾云驾雾般从龟背上被甩好在张君宝身怀绝技,连忙运转太平经,施展幻脏东西真影诀,身形踉跄,方才险险地落在地上。他站稳身形,心中暗自庆幸,若非自已反应及时,恐怕此刻已受伤不轻。他抬头望向汤普郞,眼中闪过一丝寒意,这场争斗,看来是难以避免了。
张君宝落地之际,心中微惊,却也不失冷静。他深知此刻不宜轻举妄动,便静静观察着汤普郞的动向。汤普郞见张君宝落地,也不废话,当即纵身跃起,脚中的长枪瞬间化作二三朵碗口大小的枪花,直刺向张君宝。张君宝仓惶间屏息凝神,单脚从背上捞起包裹君宝小斧的麻布,那麻布如同飞蝶般紧接着,他迅速运转太平经,体内的炼气三层气旋骤然涨大,缓缓旋转起来。一时间,他周身气息涌动,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凝聚。面对汤普郞的凌厉攻势,张君宝并未露出丝毫惧色。他深知自已与汤普郞之间的实力差距,但他并不打算就此退缩。他深吸一口气,眼中闪过一丝坚定之色,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