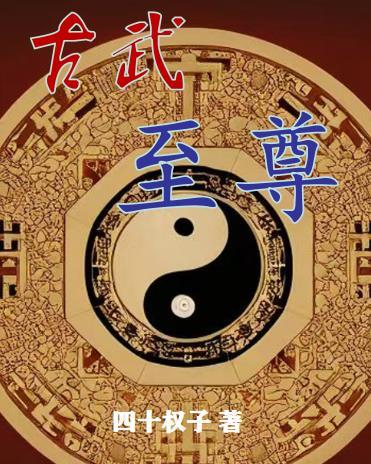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穿越之幸福日常晋江 > 第89章(第1页)
第89章(第1页)
易鸿又好笑又无奈,知道自己再说什么也没用了,便起身给他掖了掖被角,吹了油灯走出去并将门关好。
屋里黑漆漆的只有点点月光透进来,易远无声的咧了咧嘴,翻了个身睡觉。
早上早早的起床,易远挠了挠手臂,觉得很不爽。
现在已经是夏天了,晚上要听虫鸣蛙叫已经很不爽了,结果还有蚊子来凑热闹。昨天晚上睡到后半夜就被蚊子给闹醒了,好不容易睡着,今早又被后边小林子里早起找虫吃的鸟给叽叽喳喳吵醒。
烦透了。
“哥,我手上被蚊子咬了,痒死了,你看都起包了。”易远一边挠一边哼唧,好难受。
“哎呀你快别挠了,瞧瞧皮都被你给挠破了。”易鸿看见他手臂上已经被挠破皮的地方皱眉,“咋这严重啊,肿这么大。”
“那蚊子一定有毒。”易远看着手臂上肿起来的地方欲哭无泪,这也太倒霉了。原身也不是没有被蚊子叮过,顶多就是痒而已,怎么到了他这里就又肿又痒了呢。
“这怕不是蚊子叮的。”刘小燕手里拿了一个小罐,里面装的止痒的药膏,这是村子里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偏方做成的,挺管用。
“不是蚊子?那是什么东西?”易远小心的伸手戳了戳肿起来的小包,嘶了一声,“难道是什么虫子?”
刘小燕仔细看了一眼,点头,“我觉得有点像是毒拉子,那虫咬一下,可不就跟小远你手臂上这个一样吗。”
“啊?家里哪里来的虫子啊。”易远头皮发麻,他虽然不怕虫子,但是想到那虫子在自己身上这么来一下,还是感觉有点起鸡皮疙瘩。
看看手臂上的包,易远简直想哭了。
毒拉子他是知道的,其实就是毛毛虫,而且还是那种带点小毒的毛毛虫,现代东北叫做贴树皮。
“怕是后面林子里树上爬来的。”刘小燕将药膏递给自家男人,“你给小远抹点药膏,我去把早饭做上,晚点吃了饭我去找周婶子问问他们往年是咋弄的。”
“行,你去忙吧。”易鸿皱着眉头将易远拉到一边凳子上坐着,“咋给自己挠这么狠。”
“痒啊。”易远委屈的瘪瘪嘴,他也不想这么狠的对自己下手啊,但是实在是太痒了。
易鸿瞪了他一眼,“痒也不能这么狠挠,这不是你的肉啊,下那狠手,看看,这又肿又破皮的,不疼?”
“疼。”易远感觉自己都快哭出来了,“哥,这什么药啊,怎么抹那包上面了还带疼的。”
“都被挠破了可不得疼吗?”听他说疼,易鸿下手更轻了,“看你下次还敢不敢使劲这么挠。”
“还有下次啊,哥。”易远不满,一次就够让人受的了,难道做为哥哥,不该马上去给弟弟把这凶兽给处理得干干净净的吗?怎么还能威胁下次什么的呢。
明天就是结契日子了,居然给自己来这么一下,这也太惨了点啊!
“哥,擦上这个药膏之后,还会不会再痒了?”易远期待的看着他哥,一定能止痒的吧,不是传承偏方吗?
一定神效。
要是不能止痒,他都已经能想象到明晚洞房花烛跟封大哥滚床单的时候要发生的囧事了。
嘤,正在春宵噬魂销骨的时候,手臂突然发痒,肿么感觉那么囧呢,简直就是破坏气氛的杀手!
☆、结契日
村长老屋后面有个小果树林子,林子不大,种了十几棵果树。果树林边上是一块菜园子,菜园子紧挨着猪圈,猪圈跟灶屋是一起的,中间只隔了一堵墙。
而小果树林子另一边紧挨着的就是三间正屋,其中一棵桃树正巧就在易远睡的那屋窗户边上。
易远看着封哲锦拿着一种绿色的什么药水在窗户上抹,有点欲哭无泪,即使擦过药了,这手臂上还是会时不时的痒,又不能挠,忍着简直是酷刑。
“好了。”将陶瓷罐放下,一股怪怪的味道顺着敞开的窗户被风吹得满屋子都是,封哲锦闻了闻,还好这味道不是很浓,“小远,让我看看你手臂。”
“呐。”正是热的时候,易远给自己穿了一件自己做的五分袖上衣,肿起来的手臂刚好在手肘下面一点。
“还疼吗?”封哲锦想摸又怕给他摸疼,只是拿着手臂凑在眼前看了下,因为药膏是褐色的,涂抹在肿起来的地方连原本的肤色也看不出来了,因此也看不见易远早上给挠破的地方,“肿这么大,不是已经擦过药了吗,怎么一点也没消肿。”
“不知道。”易远有点泄气,看着肿了一个大包的手臂,完全不敢想象明晚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那简直太惨了。“很痒。”
“那也不能挠。”封哲锦安慰的摸了摸他的头,“我听易大哥说,你早上把这里给挠破了?”
“嗯。”易远郁闷的叹了口气,肿么能在结契之前发生这样的悲剧呢。
“先忍忍吧,这药很有效的。”封哲锦用手轻柔的在他肿起来的那一小团外围慢慢的打着转按摩,“我打猎被虫子咬了,也都是抹这个药膏,两三天就消肿了。”
易远感觉自己想晕过去,两三天?“你还是不要再安慰我了。”越说越让人想去撞墙,明天就是结契之日,晚上就是洞房花烛夜,他完全不想在中途的时候因为手痒而分神去挠手臂,想一想就想哭。“晚点消肿也没关系,能止痒不?”
这才是重点啊!
“你皮肤太嫩了。”封哲锦也没办法,被毒拉子咬了,大家都是这样擦的药,“过了今天应该就没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