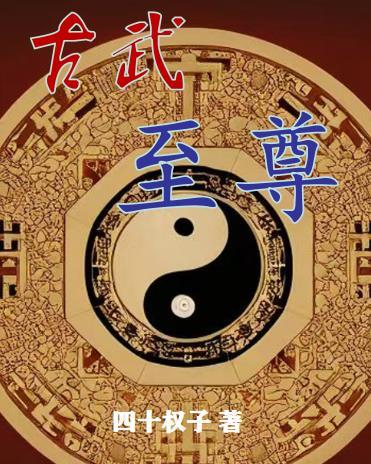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解霜雨 > 第74节(第1页)
第74节(第1页)
听见她这么说,他忽然顿住了手势,“我现在,也算你的家人吗?”
“嗯。”且惠松开他的腰,抬起湿漉的眼眸看他,“我太抬举自己了吗?”
“胡说。”沈宗良被她气笑了,“你怎么会这么想?”
她撑了一会儿,又枕在了他的手臂上,“哼。说到底还不是怪你!”
沈宗良莫名,“怎么又怪上我了?”
且惠摸了下他的喉结,“哪个叫你那么有魅力,被她喜欢上的?”
“小杨她喜欢我吗?是哪一种喜欢?”
在他的眼里,杨雨濛根本就是个跋扈的小辈。
且惠忍不住要横他一眼:“沈先生您认为呢?女人对男人,还能是哪一种呀?”
沈宗良啧了声:“她一直叫我小叔叔啊,这怎么行。”
她气他这么的双标,“怎么不行!我也一样叫你小叔叔,昨天叫了好几十句呢,在床上。”
他恍然大悟,想寻到了心病的症结,“我说呢,我这每次一碰你,那股犯罪感是从哪儿来的了,原来根子在这儿。”
且惠索性一屁股起来,“用东拉西扯来逃避罪责,就没人比你更厉害。”
沈宗良也跟着坐直,板起脸,“你这是在和谁说话?”
本来就是两厢情好时的撒娇,她看他一认真,就先怯了。
且惠的手指点在唇上,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是开玩笑的。。。。。。没有要。。。。。。。”
沈宗良掌不住笑了,“看你吓得这个样儿!”
“吓死人了。”且惠心头突突跳着,往他身上靠过去,“你不许凶我。”
“不凶,不凶。”沈宗良抱着他的心肝儿慢慢摇着,“你这么乖,我哪儿舍得凶你。”
且惠在他怀中傻笑,“那我做什么都可以吗?”
“不打紧。天漏了我也给你去补。”
珠帘外的梨木桌上,三足鼎香炉里烧了半夜的龙脑香仍有余热,清清凉凉的气味散开来,风中隐约吹来一阵小曲,且惠闭目听了听,仿佛是一组“四梦八空”的调子。
“恩多也是个空,情多也是个空,都做了南柯梦。”
京市的一月份是最冷的。
这一年交九过后,天就没怎么放晴过,陆陆续续地下着雪。
且惠每天去上学,都要做两道心理建设。
一是从沈宗良温暖的怀里爬起来,二是穿戴整齐,跨过挂着霜冻的一段路,坐到车上去。
这天期末考,她只剩下了最后一门。
昨夜复习到很晚,站在洗漱台前刷牙时,且惠困得眼都睁不开。
她拿上书包走出去,隋姨把保温杯递给她,“且惠,好好考啊。”
住了这么长时间,她把这个乖巧的小姑娘当女儿一样。
且惠接过杯子,“隋姨,你泡了什么呀?”
“二哥儿拿回来的野山参,喝了补气的。”
她塞进书包里,戴上手套出了门。
且惠站在车门边,回头冲隋姨摇摇手,“我走了,天冷,您快回去。”
上车后,方普说:“钟小姐,考完准备回家过年了吧?”
她点了点头,“是啊,看看买哪天的机票。”
到了教室前,她把书包放下,拧开瓶盖喝了一大口。
一股苦味直冲脑门,与她天天喝的中药不分伯仲。
且惠嘶一声,顿时就清醒了不少,一张卷子越写越精神。
考完,她接到幼圆的电话,问中午哪儿吃饭?
且惠一边收拾书包,用肩膀夹着手机说:“沈宗良出差去了,不在家,我们上外边吃吧?”
幼圆巴不得,她说:“好啊,吃完你陪我去爱马仕看秀吧?”
“行,反正考完试了,我休息两天。”
“那更好,晚上酒吧玩儿一趟,完美!”
她们去国子监吃淮扬菜,坐了冯家的车。
且惠想,方伯平时接送她也辛苦,能休息便尽量叫他休息。
这家店是新开的,人均消费在两千往上,贵得离谱。
且惠翻着菜谱,也不怎么瞧得懂那些菜名,随便点了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