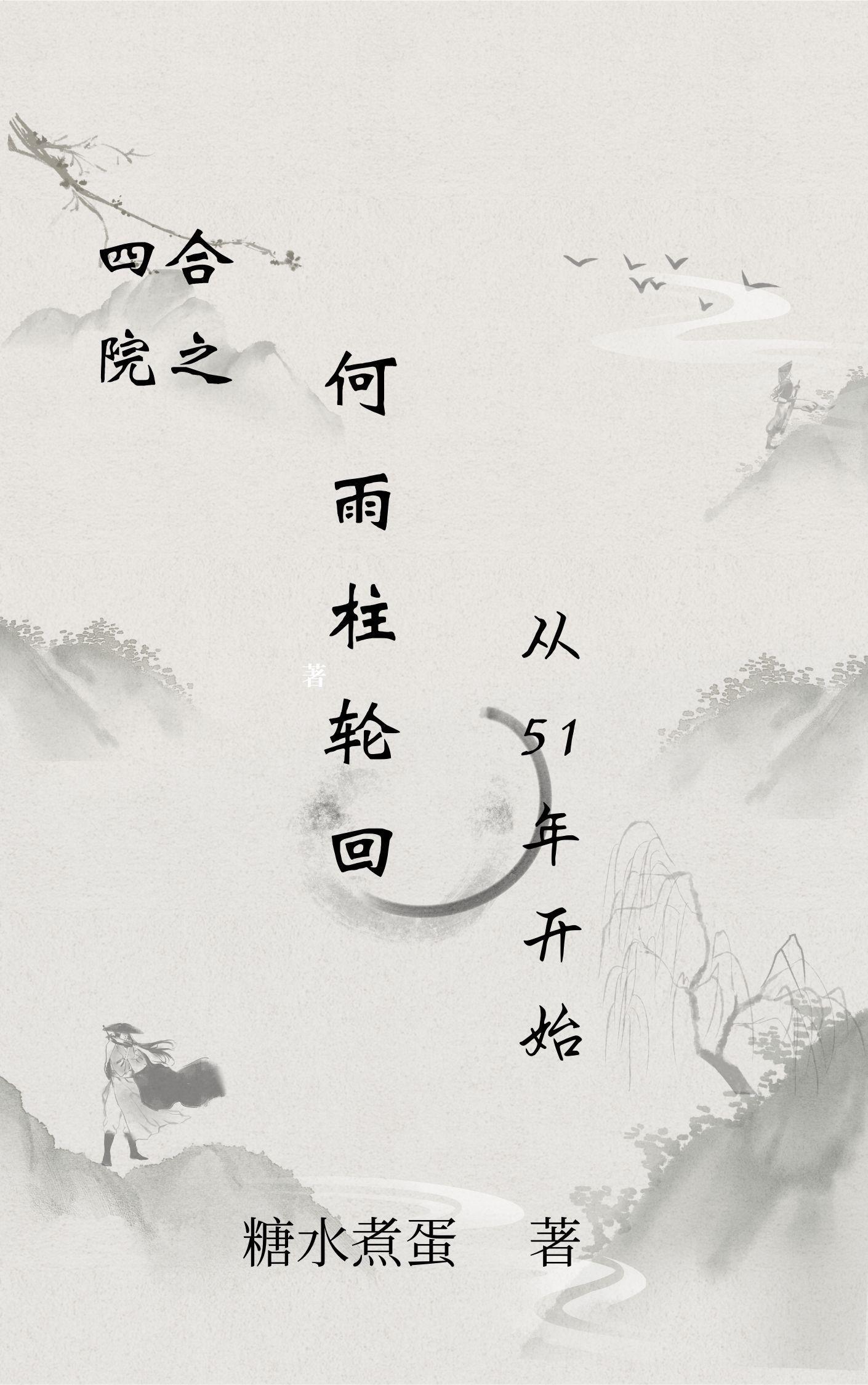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穿成笔下最惨美人受后免费阅读全 > 第184章(第3页)
第184章(第3页)
苏陌听得入了耳,便推开窗去细瞧,但见那小生继续唱道:“落灯花,棋未收,叹新丰孤馆人留……”
哪知戏台下的看客并不买账,已是嘘声不断。
“唱的什么!下来!谁要听你唱哀歌!”
“不会唱别唱,退钱!退钱!”
“喂!我说别整这些悲风伤秋的,太煞风景,来点才子佳人,春宵一刻值千金呀!”
“据说是乐坊班子里新来了个作词人,自负有才,写的词曲却无人买账。”沈子承递上一盏新茶,说道,“那作词人过去也曾是济州府的名门,家道中落,如今只剩下他一个,过得比乞丐还不如。”
苏陌叹道:“可惜了,写的一手好词。”
台下起哄的闹得越起劲,看热闹的也看得越起劲。
那唱曲的伶人小生羞得满面通红,已是眼角垂泪,快要哭出来了。
“这不欺负人吗?”凌舟气得脸都红了,“在不夜宫可没人敢这样!”
李荀看了看凌舟,又看了看戏台上那个可怜人,抡起拳头便要去打抱不平。
凌舟忙给他拉住了:“出门在外,不可给公子惹事。”
正闹着,听得前头一阵骚乱,一个衣着褴褛的书生被人从后台一脚踹了出来。
“滚吧您呢,自己几斤几两不知道,还敢来要钱?”
那书生摔在地上,鼻青脸肿的,很是狼狈,他捡起扔在地上的词谱,爱惜地用衣袖擦了又擦,右手很不自然地垂着。
凌舟定睛一看,那不是谢大才子,谢一凡吗!
谢一凡当初可是不夜宫的座上画师,帝城求一画而不可得的国子监第一画手。
他怎么落得这般田地?
凌舟不知道这个闲事该不该管,但见那谢一凡走路一瘸一拐的,实在可怜,便拉着李荀跟了上去。
到了他住的地方,凌舟更震惊了,谢一凡竟然同一群流浪汉窝在一所叫做“寒馆”的破房子里,一卷草席一个破布包,便是他的全部财产。
凌舟思虑再三,决定告诉公子。
“谢一凡?”苏陌刚同沈子承聊完,听到这个消息颇为意外。
他毫不犹豫道:“带我去见他。”
自永寿宫《春宫图》一事之后,苏陌便忘记了谢一凡,如今再次听到他的消息,心情极为复杂。
走到寒馆之外,苏陌转身对裴寻芳说:“不可为难他。”
裴寻芳明白他的意思。
甫一进去,便见满屋子烂草破布,透着腐臭味儿。
蜘网密布的墙角,三个醉汉正围着谢一凡,调戏道:“瞧你细皮嫩肉的,跟了爷几个,包你吃喝不愁,整个济州府再不会有人敢欺负你。”
谢一凡手里拿着根断枝,挥舞着:“士可杀,不可辱,尔等泼皮休想辱我!”
“嘿,给脸不要脸!”那醉汉蛮横起来,“今儿个爷便要拿你泻泻火!去,把他裤子给老子扒了!”
另两人恶虎一般扑了上去。
苏陌厉声吼道:“住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