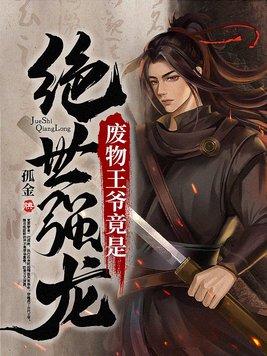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女扮男装拿稳权宦剧本免费 > 第10章(第1页)
第10章(第1页)
此时,窗口附近便只剩这么两桌人。
千闵提起茶壶斟茶,低头送至白惜时面前,白惜时气定神闲,端起茶盏喝了一口。
蒋寅见方才挑衅的未得回应,不甘心,这回直接开口。
“没想到兄弟门出来乐呵乐呵,于此处竟遇到了厂督。厂督白日日理万机,夜中还来狎妓玩乐,但属下以为,厂督不宜操劳过度,以免伤身呐。”
此言一出,除了滕烈,其余几个锦衣卫均哈哈笑了起来,太监没有那家伙事,又谈何伤身?
蒋寅分明是看白惜时年纪轻资历浅,不把他这个厂督放在眼里。
但他之所以敢公然叫嚣,究其根本,还是取决去指挥使滕烈的态度。
按照惯例,锦衣卫向来听令于东厂,但因前任东厂厂督与锦衣卫指挥使合谋犯案,皇帝似乎不希望东厂与锦衣卫走得太近,因而在人员任免上也用了一番心思。
滕烈,出自勋贵之后,家族世代簪缨,二十二岁便担任禁军首领,二十四岁提拔为锦衣卫指挥使,为人桀骜不驯、恣意无拘。
而白惜时在背景、资历上显然不如滕烈,年纪也不占优势。
简而言之,滕烈不服白惜时。
以至于形成了当前锦衣卫不大听从东厂调遣的局面,白惜时自上任以来,确实感受到了这方面的掣肘。
滕烈此人,白惜时一时半会还没想到拿捏拉拢之法,但并不意味着,她就能被人骑在头上打压。
闻言,白惜时扬唇抬眸,视线投过去,带着一股阴恻恻的狠。
她睨着蒋寅,“既然自称一声属下,就该清楚,咱家不仅可以狎妓,若是不挑,亦可狎你。”
这话说得张狂,直接将蒋寅比喻成那供人狎玩的妓子。
蒋寅愣了片刻,他生得人高马大,没想到有一天竟会被个不男不女的太监如此贬低,
瞬间气得面红脖子粗。
“你说什么,你……”
滕烈此前一直未语专心赏曲,直到这时候才伸手,拦下就要往前理论的蒋寅。
“下头人不懂规矩,厂督担待。”
男子声线低沉轻慢,口上虽说着道歉之语,然神色倨傲散漫,显然未将白惜时放在眼里。
说罢她点了点身侧美娇娘,一指对面,“搅扰厂督雅兴,蝶娘,替我去给厂督敬杯酒,赔个不是。”
蝶娘已从方才的对话中知道了白惜时的身份,同样也明白滕烈的势力,此刻夹在两方中间,十分为难,她怕贸然过去,会遭白惜时记恨。
毕竟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滕烈根本不是真心实意道歉,如若真心,他当自己过去。
可眼下他仍然端坐如初,连个身子都未起。
女子拿酒杯的动作出现了几分迟疑。
“蝶娘放心,既叫你去,定会护你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