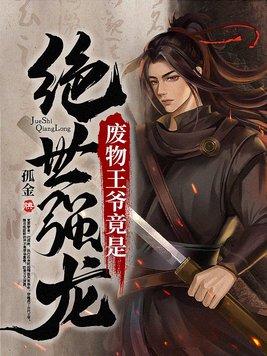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折四字词语 > 第65章(第1页)
第65章(第1页)
福嘉心中一凛,猛然抬起头。泪珠没来得及抹去,还堪堪挂在她眼眶中。
李亨像是未见她的诧异,继续说道:“福嘉,俊俏郎君多的是,众望所归的将星难寻啊,况且现在……没有时间了。”
福嘉摇摇头,她怔怔地反驳:“阿耶,兰烽他之所以忠心耿耿的卖命,是因为他喜欢上了我,因为我对他好。若是把他强行留在环州,与我分开,他或许……”
或许一如前世,因为某些机缘,成为叛将敌首。
李亨笑了:“并非如此,傻孩子。他之所以对大周皇室忠心,是因为曾有一位皇室公主救过他的命。”
福嘉身体僵住:“救过他,谁?”
李亨道:“好多年前,你在金明池,因救人落水,还记得吗?”
福嘉没有说话,落水之后,她感染风寒,烧了数日,很多事都记不清了。
李亨缓缓转动脖子,骨头发出轻微的咯吱声,看向一侧空处:“救上来的孩子,就是兰烽。”
一种透彻的凉意攫住她,福嘉木然动着唇:“……您说什么?”
“你救过他。”
李亨心疼地看着女儿,忍着不适,一口气把话说完:“孩子,在与你成亲之前,兰烽就已经把命给你了。对男人而言,喜欢谁并不那么重要,他现在喜欢你,以前未必没喜欢过别人,年轻时把情爱看得重,年长后未必不会因为一事无成而迁怒于你。我是你阿耶,才会同你说这些话,你回去仔细想想。”
福嘉走出勤政殿,夜风仿若刺骨,她有一瞬间,觉得自己走在冰天霜雪中。
即便是穗穗,也知道这时候不该多嘴,她看着福嘉脸色乌青,唇色发紫,只能小心翼翼用披风包住她。
两人一直走到宣德门附近,抬辇的武官和随侍跟在她们身后。福嘉忽然毫无征兆地落了泪,她阖目,心中忿念杂乱,却又空空如也。
穗穗终于忍不住,她一边替她抹泪,也跟着落泪:“殿下不要哭了,殿下……”
福嘉像被自己养的小花猫舔了一口,她含着泪笑了一声:“傻子,你哭什么呢?”
穗穗拉着她的手:“殿下心疼阿耶,婢子心疼殿下。”
记忆中冬日讨碳的小娘子,与眼前人重合。福嘉明白这时候不该沉湎于私情,她还想好好地活下去,保护她的人。
包括兰烽。
“随我去看看皇后嬢嬢”福嘉舌尖一顿,加重了语气:“过得好不好。”
一行人走到外城道观,道观已经被太子的人重重包围。为首的是东宫朱虞候,见了福嘉,他行礼道:“殿下,里面的大人形容不佳,恐怕惊扰凤体。”
福嘉也礼貌点头,步子却没停下:“不打紧,我胆子大。”
她从穗穗手里接过白绫,莲步轻移,悠然走近。
雕花门打开,她却没再入内。
屋里散发出一股恶臭,曹皇后独自一人趴在榻上,面朝着墙面。她听见声响,慢慢翻身过来,看着福嘉。
曹皇后近来在服侍的宫女脸上看到过无数次恐惧和惊悚。
福嘉神色却是变也未变,她捏着白绫走进来,蹲在她床边,柔声问:“嬢嬢,你怎么变成了这样?”
曹皇后喉中,仿佛发出了皮肉撕裂声,她抬起血肉模糊的手,放在福嘉肩膀上,费尽全力道:“当然是,是因为你……那个宝贝驸马。”
提起那个人,她怒不可遏,几乎短暂忘却了疼痛:“他迫我……吃了好多种蛊虫……”
福嘉没有避开这只手,也不怕对方弄脏她的裙子,她勾了勾唇,惋惜:“竟然是这样。”
她将白绫绕回袖子上,喃喃道:“我本打算亲手送你上路,如今看来,没必要了。”
曹皇后听罢,又发出一声尖叫:“福嘉,你给我个痛快!”
福嘉拨开她的手,不情愿道:“嫁鸡随鸡,我听我夫君的。”
曹皇后翻身滚落,抓住福嘉衣摆,她断断续续的诅咒道:“你别以为你能有什么……好下场,他可不是良善之辈,他,他手段残忍……”
福嘉居高临下地看着她,不同意她的话:“嬢嬢,你误会了,他很好的。他只是为了我,什么都可以去做。”
她说罢,便抬脚欲踏出门槛,听见外面有人说了什么,接着道观内的宫女黄门们一起跪下。
穗穗见福嘉出来,膝头挪过去,小声道:“殿下节哀,陛下,陛下薨了……”
仿佛一盆凉水兜头淋下来,福嘉冷得遍体生寒,她在原地站着,泪水难以抑制的漱漱滚落。
白绫还捏在手心,福嘉说不上来是什么心情,对李亨,她恨过怕过,也时时能感受到他对自己留有温情。
可这一切都结束了。这瞬间她忽然明白,李亨为何一再逼问她对兰烽的感情——若她真的爱他胜过理智,他终究还是顾念女儿,不会狠心让他留在环州。
福嘉睫毛轻颤,慢慢挪动步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一直走出道观。
*
西北边关已近入冬,没有福嘉在身边,兰烽这段时日住在环州军营中,与将士们同吃同住,过得很糙,好像又回到在并州戍边的生活。
兰烽一接李亨薨逝的消息,就同环州宣抚使告假,快马加鞭往西京赶。
送信来的是他留在西京的亲信,那人还告诉他,曹后自戕殉了陛下,大皇子在不久后也因放纵过渡夭亡,福嘉殿下得到消息,没说什么。
兰烽焦灼稍定,政敌都已亡故,如今朝中没有年岁合适的储君,太子登基应当是板上钉钉之事。北方两路军事重镇,一个在赵端平手中,还有一处在自己手中,短时间内不至于拖后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