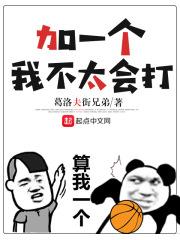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掌中雀在线阅读 > 第51章(第1页)
第51章(第1页)
“原来我早就让梁四爷养着了,”韩墨骁抬手摸过冰冷的玻璃罩子,“您在大洋彼岸抬我的场,我见什么都卖得出去,竟以为是自己什么都写得好。”
梁今曦看向他,深沉的目光像要射进他灵魂里:“白墨卿死后你就不写了,他对你很重要?”
太久没从别人嘴里听到这个名字,韩墨骁心中一颤。白墨卿是白家长子,也是他名义上的大哥,梁今曦却依然明知故问。
大抵因为白墨卿死后,他把那个“墨”字摘进了自己名字里。
韩墨骁垂眸不答,反倒也去戳人肺管子:“梁四爷,听闻你和两位哥哥感情深厚,他们去世之后,你还能和以前一样快活?”
梁今曦眉头一锁,还握着他腕子的手也不自觉地用了点力。
和韩墨骁第一次上床那天,梁今曦确实是和他有仇的。他存心报复他、打算碾碎他最后一点尊严,所以问出了那句“不知道人懂不懂得叫人高兴”。
后来他在床上控制他、重重地惩罚他、狠狠地欺负他让他痛、让他哭、让他承受不了。
他要问问二十二岁、同被命运敲断了腿的韩墨骁:
“你如今,读得懂你当年写的那幅猖狂至极的《西江月》否?!”
他们一个以身典命,并不知道对方早已怀抱他无意间招惹出来的恨意;一个把对命运无常的无力和愤怒加诸于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身上,就这样开始了一场冰冷丑陋的交易。
如今梁今曦那点莫名的恨意早已散去,韩墨骁也求仁得仁保全了逢春院,直到今日才把这点前缘揭开。
偏小韩院长又报复似的,提起了梁四爷最碰不得的回忆。
接下来一分多钟都无人说话。
韩墨骁的手被梁四爷捏得连骨头都疼,也顾不得人还在生气,又冷冷问:“那《将进酒》呢?”
李太白那么多名作,偏偏要选这一,偏偏要让他再回忆起他最碰不得的回忆。
第28章
“你见过了,挂在书房,”梁今曦神情冷淡,松了力道放开他,“你还是行草写得最好。”
当初的拜帖是用端正的小楷写的,规规矩矩、却也束手束脚,若非某些笔画处有些独特的小习惯,梁四爷差点没认出来。
韩墨骁揉着被抓出几道指印的手腕一愣:“你不是故意要我写的?”
“故意?”梁今曦不解,“有什么典故?”
韩墨骁又看了他一会儿,确认他没有说谎。
他也没必要说谎,因为就算是故意的,韩墨骁也只能老老实实替他写,看来点那诗真是误打误撞。
想到这里,韩墨骁脸上又火辣辣地烫起来,刚才他实在是反应过激了。
初看到这满墙满壁的书法,他震惊之余,思绪立刻回到了在欧洲的那段荒唐而快乐的岁月,马上又想到他大哥的枉死,想到他因此重坠地狱的人生,满心都是悔恨和痛苦,连带着对眼前这人都怨起来。
可是梁今曦却在他不知道的地方和时间里,将他的作品一幅一幅收集起来,有一些连他自己都不记得写过,这个人却把这些游戏玩笑之作慎重其事地和那些价值不菲的宝物保存在一起,在无人知晓的地方替他这个并不高明、不认真的所谓书法家开着作品展。
他却只是朝他怒、嘲讽、质问、用他的伤口刺痛他。
实在幼稚而可笑。
“是我错怪了,”他臊得满脸通红,恨不得给自己一耳光,抬眼看着人诚恳地道歉,“对不起,四爷。”
“认错倒快,”梁四爷见他这般,倒也气不起来,看他实在有些难过了,便又揶揄道,“嘴上说对不起?” 韩墨骁眨了眨眼,走过去垫脚在他脸颊上印下一个浅吻。不同于往常,这回多少有了点真心在里面,手也牵住了他的手,又因为紧张和别的什么,不自觉地颤抖着,指尖冰凉,手心出汗。
他动了动眼皮,睫毛跟着颤了颤:“谢谢。”
梁今曦瞥他一眼,勾唇道:“谢什么?”
韩墨骁觉得心脏都跟着颤抖起来,低声说:“不知道。”
谢什么呢?
谢他这么珍惜他的笔墨,谢他替他收藏了他最肆意的一段时光,谢他懂他的行草,还是谢他让他知道,他们并不是随便是谁都能睡得下去,而是早早选定的对方?
他不知道,但是心里很满,挤压得颤、疼痛,他死死地抓着梁今曦的手,指甲都陷进他的皮肉里。
梁四爷转过脸来看着他,两人四目相对、呼吸交缠。
虽然两人见面时多半都要做些禽兽的事,可实际上梁四爷冷眼冷脸的时候更多些。哪怕说着浑话,哪怕在床上干得热火朝天,韩墨骁偶尔瞥见他的眼睛,也总觉得里头的冰没有彻底融化过。
此时他眼里常有的冷意都散去,唇边似笑非笑的暧昧恰到好处,好像在暗示着什么,又不是那种要把人办了的感觉,特别容易让人沉迷。
韩墨骁不得不承认这人长得有些过于英俊,又是一个比他成熟太多的男人,稳重且矜贵、风流又淡然,本就容易让人同为男人的他羡慕又向往,此情此景再和他对视,实在不太妙。
他别开眼,白净的脸涨得通红,心跳得咚咚直响。
梁四爷瞧着他的脸、脖子、耳朵慢慢地全红了,连手指头都泛起了粉,也不再追问,只是拉过他的手放在掌心把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