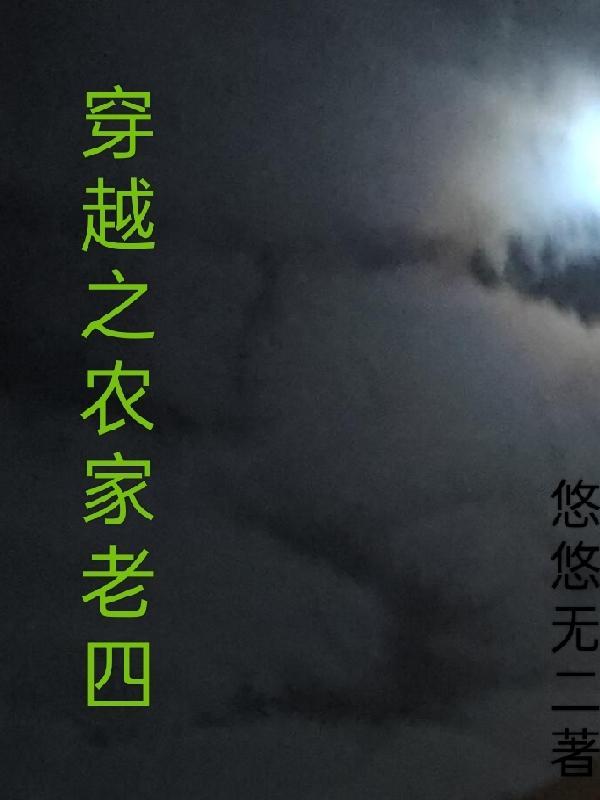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质子皇后 > 第10章(第1页)
第10章(第1页)
“这……我也不知。”贺兰辛如实道,“我看沈公子带了不少书,大约是爱书之人。甘罗十二为上卿,文姬六岁辨弦音。沈公子已及束发之年,若是天纵奇才,博览群书,学富五车,也不无可能。”
段曦宁摸着下巴思量着:“来之前,太傅让朕寻竟陵先生回去,可朕派人私下里搜了几遍都没找到这老小子。沈渊既是他的侄子,大差不差,带回去应当也是可以的吧?”
听了这话,贺兰辛嘴角抽了抽,伯父跟侄子,声望上就差了一大截,哪里就大差不差了?
他忍不住提醒:“陛下,沈七公子毕竟不知根底,学识名望也比不上竟陵先生,只怕太傅那儿可不好交代。”
段曦宁默然不语,眸色幽深,喃喃着:“关乎我大桓文治,那便只能再累太傅几年了。”
沈渊并不知自己在其他方面被惦记上了,频频走神,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那荆国质子的事,手中的笔停在空中许久都未曾动。
“公子,公子。”商陆见他神情呆滞,唤了几声,将自己写的几个大字递给他,“你看我写的行吗?”
沈渊回过神来,低头便看到面前桌子上的纸上落了一团墨,立即将手中的笔放下,把弄脏的纸扔掉,这才接过商陆写的几个大字来看。
看到纸上还算工整的字,沈渊这才点点头:“大有长进。”
商陆面上一喜,好奇地问:“公子,你方才那么出神,想什么呢?”
沈渊神情微顿,放下了手中的习字,抬眸问:“商陆,你听说过荆国质子吗?”
“荆国质子?”商陆诧异,“荆国不是被灭了吗?哪里会有质子?”
沈渊拿出了那把匕首放在了桌子上:“那位女皇陛下说,这便是那荆国质子的东西。”
“荆,荆国质子的东西?”商陆吓了一跳,“荆国皇族据说已经被族灭,这,这岂不就是,死人用过的东西?”
沈渊忙告诫道:“当心祸从口出,慎言。”
看着眼前的匕首,他思索着段曦宁到底有何用意。
是为了警告他别生不该有的心思,以免不得好死。
还是,随手扔个不想要的匕首而已?
这匕首并无珍贵之处,能到她手里,那荆国质子约莫不是国灭身死那么简单,或许还有什么外人不知的隐情。
个中祥情,又该从何得知呢?
许是物伤其类,一向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他,极想知道那位荆国质子的事,却也不敢在大桓的军营中随意打听。
大桓新得荆国之地,诸事繁杂,千头万绪皆须理清。
段曦宁安排好各州郡大小官员、驻军将士,厘清各州官府文书,便费了好一番功夫。
实在是出征时她嫌累赘,带的文吏不多。此次战事太过顺利,吏部派来的官员还未到,眼下只能一个人当三个人使,将读过书的将士都拉来干活。
只是,这活儿干着干着,脾气本就不好的段曦宁便暴躁起来。
中军大帐时常传来她骂骂咧咧的声音,叫人靠近大帐便心有戚戚焉。
“叫你平时多读书识字,你都读到了狗肚子里,七个字儿能写错六个半,认那几个字儿都叫你当下酒菜了啊!”
“你算的什么狗屁账,三十万的账给老子算成五十万,缺的银子你补啊?”
“这安民告示写的什么玩意儿,糊弄鬼呢?”
“看你划的地界叫什么?你当百姓是牛羊,想往哪儿赶往哪儿赶?朕把你当头羊撵了得了!”
“全杀了?全杀了你一个人给老子干一万人的活儿?你咋那么能耐呢?”
“滚滚滚,睁开你那俩眼珠子好好瞅瞅!写的都是什么鬼画符?”
叫这些五大三粗的将军来做文吏书生的活儿,属实有些强人所难,常做得错漏百出,惹来一顿臭骂,让他们叫苦不迭。
可是对着他们通宵达旦、宵衣旰食的陛下,对上她那趴在书案上只眯了不到一个时辰的脸,他们再有牢骚也瞬间咽了回去。
陛下尚如此,他们又哪里敢懈怠?
好在,段曦宁安排好驻军事宜,留麾下大将韩新柏驻守武康之后,终于要班师回朝了
这下,众将士策马扬鞭只觉轻快,恨不能一日千里转瞬就回帝都云京。
段曦宁是个除了正事其他都懒得动的主,回朝路上干脆成日里躺在马车上蒙头大睡,只偶尔听臣下回禀正事。
浩浩荡荡的回朝大军中,唯二如她这般成日待在马车中不怎么出来的,也就只有沈渊了。
他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生怕行差踏错惹来祸端,便成日里闷在马车中看自己带的书,恨不得自己化作一阵清风,烟消云散。
哪怕是过江之前,大军安营休整,他也只躲在自己帐中从不出去。
共乘一骑
这日,沈渊独自在帐中看书时,刚落笔写下一句诗,便听得有人进来了,不慌不忙地将诗收好。
还以为是商陆回来了,一抬头,竟是段曦宁。
没想到她竟会纡尊降贵地来他的营帐中,他惊得好半晌未反应过来,一动不动,呆呆地看她进来。
回过神来,他急忙起身行礼,段曦宁摆了摆手道:“不必多礼。”
桓军在此地准备过江的战船,须得扎营几日。段曦宁难得清闲,在马车上也睡了个够本,便出来活动活动筋骨。
一闲下来,她才想起来自己还从梁国带了个质子,又听贺兰辛说沈渊都把自己关起来从不出门,好奇地过来看看。
她虽点他为质子,却不是要他做囚徒,自然也不需要他画地为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