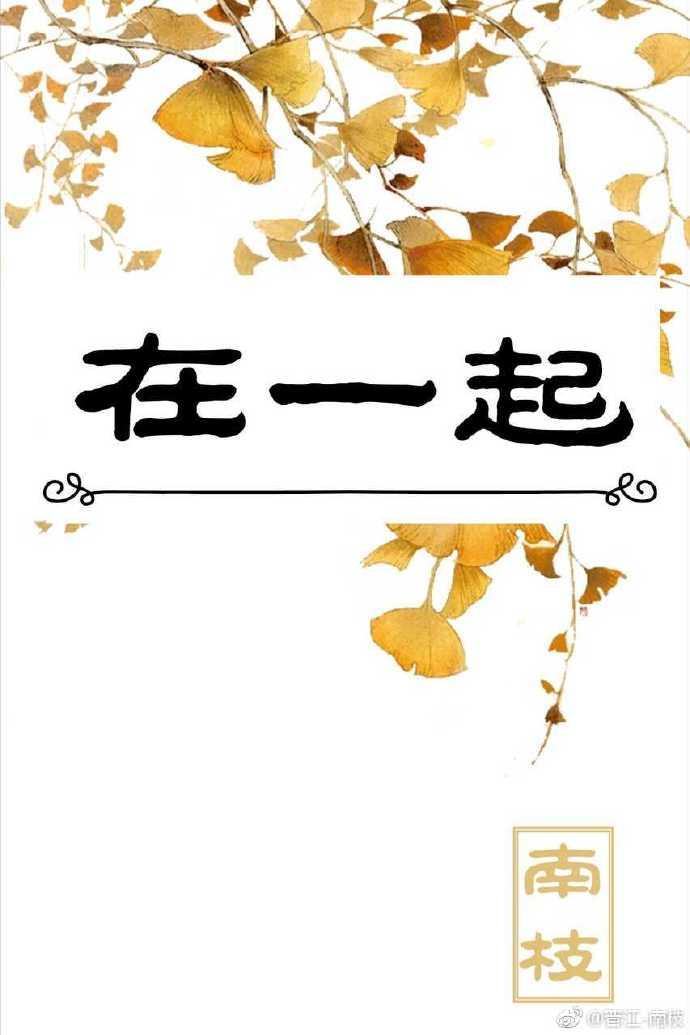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万人嫌和万人迷he了[快穿 > 第40頁(第1页)
第40頁(第1页)
宋清淮仍然安安靜靜躺在那裡,無知無覺像一幅折損的美人畫。
思緒開始翻騰,這半年來經歷的一切猶如走馬觀花。
六月份的某天,一份監控送到他面前。
五年前,本該在千里之外出差的宋徽商,半夜來到傅家夫婦所在的漁村。
在他離開後不久,傅家夫婦死於二氧化碳中毒,第二天才被發現。
宋徽商托關係刪掉了這一行程記錄,這事兒誰也不知道。
辦案負責人走了過場,勘察現場得出結論是,沒有第三方存在痕跡,宣布為自殺。
他連父母最後一面都沒見到,更沒留下隻言片語,一夜之間,他成了沒有家的流浪狗。
後來宋徽商幫他操持的葬禮,又收購了群龍無的傅氏集團。
利益是悲劇的永恆課題。
如此種種,他實難自我說服。
他已做好打算,收集證據重啟舊案,不管如何做一個了斷,慰藉父母枉死的冤魂。
可是,宋清淮,宋清淮……
傅識均垂端詳,他清醒的時候,兩人唇槍舌劍,誰也不讓誰。
宋清淮瘦了,下巴尖尖兒的,像被霜雪打了的玫瑰。脖子以下被完全包裹,只露出了一點點泛白的指尖。
這雙手曾經演奏出驚動世界的音樂。
他的仇人此刻躺在病床上,他該高興的。
窗外的風很急,唰唰唰打在玻璃上。傅識均臉色灰敗,乾燥起皮的唇瓣黏在牙上,繃成了一個苦痛的弧度。
「淮淮,我這輩子都不會放手。」
恨也好,愛也罷。
感情這個課題,沒人能給他一個標準答案。
他已是個病入膏肓的瘋子,就這樣互相折磨、互相取暖,這個冬天才不會這麼難挨。
痛苦的呢喃消散在空氣中,病房門敲響。
護士進來換藥,她有些訝異,零下二三十度的天氣里,傅識均竟然只穿了一件襯衫,這得多緊張匆忙。
「您受傷了,我給您上個藥吧。」
傅識均按了按受傷的嘴角拒絕了。
「誒,」護士想告訴傅識均宋清淮生病的事,但是又有保密原則在,只能委婉地提醒,「多注意一下病人的健康。」
傅識均應了一聲,沉沉盯著手機里的未接來電,離開了病房。
宋清淮睡了一天一夜,擺脫了夢境清醒後,跌入了另一個噩夢。
「老師,我怎麼了?」
宋清淮全身動彈不得,像困在牢籠里的小獸,迷茫地望向眾人。
「宋先生,冷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