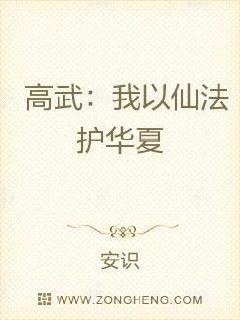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浮生尽处全文免费阅读 > 第十一章 陌路(第3页)
第十一章 陌路(第3页)
“义父多虑,他年纪尚幼,假以时日,必定能成大器,我会一直伴你们左右。”
墨斐凝视着他诚恳的眼神,心中不禁一阵感动。
离开墨府后,脚下的步子开始换慌乱,他害怕再晚一步,佛柃恐怕已经命悬一线,他第一次这么害怕,会让苏衍伤心。
“柃儿你要记得,你弟弟他没有爹爹疼,也没有聪明的娘亲,不能给他将来,你是姐姐,你要好好照顾他,别让他流泪。”
“姐姐是谁?弟弟又为何流泪?”
为什么?!
那个躺在牢里的人奄奄一息,背上布满鞭痕。似是被什么刺激到,她猛惊醒。
睁开沉重的眼皮,一片暗灰色的视线中,那个人居高临下:“姐姐,你不是不屑正眼瞧我吗?今日,我得好好让你看着我,看看我是如何折磨你,让你受尽百般折磨!”话音刚落,他扬起铁鞭便抽了下去,佛柃闷哼一声,却硬是不求饶也不喊痛。
“你不是很高傲很厉害么?现在却被我踩在脚下,这种滋味如何?”
佛柃艰难的支撑起半个身子,却还是那样清冷孤绝,似乎世上再肮脏的东西,也污染不了她一寸。她冷漠的盯着他,突然挥掌劈去,将手中早已暗藏的银针拍进他的脚踝。银针作为暗器,必然是涂了毒的,加之佛柃用尽了全力,歌弈剡瘫倒在,痛得冷汗直流,他立即运功护住心脉,暂时缓解了毒液汇入五脏六腑,可即使这样,毒素也蔓延到了四肢,脑袋里像是嵌进了炸药,好似随时会将脑浆炸裂。
他对她咬牙切齿道:“你跟言真一样,学了一身见不得光的东西,你们不配做王府的人!”
佛柃的嘴角勾起一抹笑意,眼里却无一丝痛快,只低声笑着。
歌弈剡强忍着痛:“歌佛柃,我与你从来势不两立,你可知为何?”他嘴唇泛白,大颗大颗的汗珠滚下脸颊,“你是我这辈子最恨的人,最恨的人!”他冲晃着去兵器架上拿下砍刀,转身就要向佛柃砍去。
哐—
手中的砍刀被打落,还没找到暗器飞来的方向,他的面前就已被一个黑影控制住,他吓得立即弯腰去捡武器,手刚握住刀柄,一只黑靴恰好踩住他的手。
歌弈剡抬着头去辨认此人,眼前却始终是模糊一片。
“不用看了,是掌事大人来了。”砚生将刀踢到远处,对跪在上的人说。
“你来干什么?起开!”
左卿冷冷道:“来干什么?不如你自己去问问义父。”
歌弈剡一听是舅舅了话,更是大为光火:“杀了她对舅舅百利而无一害,恐怕舅舅是听了谁的妖言,被蛊惑了心!”
左卿平静看着他,眼里波澜不惊,“你若意气用事,言真定不会放过你,你想死可以,别拉上我们!”
歌弈剡紧握着双手,手背上的青筋因愤怒而暴起,若不是因为自己受了伤,左卿这个连兵器都不会握的人怎么可能救走佛柃!可是自己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将自己做梦都想杀的人救走。
今日少加在她身上的痛苦,明后定会十倍奉还!
他盯着左卿,忽然感觉哪里不对,但却始终想不起不对在哪里。此时伤口周围的毒已经蔓延至脖子,一阵一阵的撕裂传至大脑,他抱着脑袋,踉跄着跑出牢。
左卿走近佛柃身边,眼前的人奄奄一息,却还是奋力抬起布满伤口的手,一点点接近那一角玄袍,左卿往后一步,她的手落了个空。
她茫然看着他,眼泪突然滑出眼眶,落在上那一滩血中。
“既然无缘,何必强求?”
佛柃固执看着他,手依旧僵持在那里,眼泪越聚越多,上那一滩血水的颜色却越浓艳。
“或许这世上痛苦的是有缘无份,而你俩,无缘无份。”
她艰难的张口,却语不成句。
左卿叹了叹气,将她抱起。佛柃眼里忽闪过希冀,但却在他的冷漠中被击个粉碎。
曾经有人用一生的等待都没能和相爱的人长相厮守,到最后不过换来一场痛彻心扉的彻悟。
既如此,不如与君陌路,再无折磨。
虽然此时佛柃错将左卿认作西楼,他说的话并不是西楼所说,但事实却是一样,他从未爱过他,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