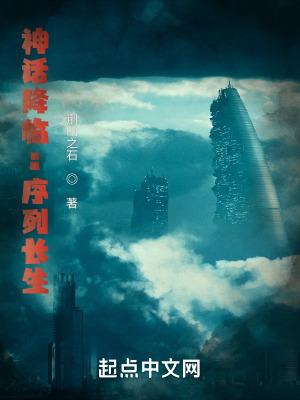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被招婿了 方便面君 笔趣阁 > 第37頁(第1页)
第37頁(第1页)
她看得出張棹歌不是故作風輕雲淡實則心生芥蒂,那輕鬆散漫渾不在意的姿態是裝不出來?的。
張棹歌的脾氣原來?這麼好的嗎?
竇嬰又扔下一道?驚雷:「大郎要不考慮一下我家七娘?」
張棹歌這下是真沒?經受住驚嚇,手中?的酒盞一個打?滑險些摔落,她眼疾手快地接住,里?面?的酒卻都灑了出來?。
她沒?想到竇嬰不是催婚,是想當月老。
這頓飯也不是普通的年夜飯,而是相親宴!
「竇嬰你——」張棹歌一邊撣去衣服上的酒水,一邊說:「大過年的別拿我們打?。再說,崔七娘本就不缺相看的人?選。」
她又看了眼崔筠。
後者坐在月牙凳上,垂著眼帘,叫人?看不清神情。
但她這個反應過於?平靜,顯然早已知?曉了竇嬰會說這話?。
張棹歌很快就猜到了她們的用意——崔七娘想要對抗世俗,與其聽從崔元峰的安排,挑選一個不靠譜的夫婿,還不如挑選一個她認為靠得住的合伙人?,將主動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是的,張棹歌已經認定了她在她們心目中?只是一個婚姻的合作者。
她們在婚姻當中?先要思考的是利益的得與失,而不是愛與不愛。
張棹歌很欣慰她們能有如此勇氣,保持如此清醒的頭腦——前提是被衡量得與失的合作對象不是她。
她私心還是想跟一個自己喜歡的人?共度餘生的。
當然,她也清楚身處在這個時代,她的私心只能成為奢望。
可?退一步來?說,就算她不奢望一份愛情,她也沒?法讓崔筠在這個婚姻當中?得到更長遠的利益——崔筠寧願跟整個崔氏對抗也要守住屬於?自己的家業,那必然很在意傳承。她是個貨真價實的女人?,沒?法跟崔筠生孩子,沒?有子嗣,崔筠可?能又得面?臨同樣的困境,還不如一開始就找個真男人?。
都是朋友,張棹歌對崔筠自然是能幫則幫,可?這婚姻大事真幫不了。
崔筠觀張棹歌神色便知?「他」並無想法,於?是趕在竇嬰開口之前,悄悄捏了捏竇嬰的手。
竇嬰轉頭看她,見她小幅度地搖了搖頭,才眸光微斂,略有些俏皮地問張棹歌:「我這說笑的本事是學?大郎的,奴家學?得像嗎?」
張棹歌:「……」
學?得很好,下次別學?了。
氣氛仍有些尷尬,崔筠便扯了個旁的話?題:「好香,不知?是不是炙羊排好了。」
張棹歌沿著幞頭包邊撓了撓頭皮,說:「我去看看。」
說罷,逃似的起身出去了。
……
竇嬰那句話?仿佛真的只是一句玩笑話?,之後誰都沒?有再提。
張棹歌認為這件事過去了,就沒?再將它放在心上。
待吃完年夜飯,距離天黑大約還有半個時辰,張棹歌問姐妹倆:「聽聞鄉里?晚上有驅儺,你們可?要去湊這個熱鬧?」
驅儺就是跳大神,會有專門的人?員扮邪祟、年獸等寓意不好的角色,然後由巫覡主持儀式,家家戶戶會沖他們撒豆子或銅錢,寓意將一年的霉運都驅散。
這個習俗一直流傳至張棹歌所生活的,這大概也是她穿越以來?,唯一能令她產生歸屬感的地方。
吃飽喝足的竇嬰一臉饜足,她慵懶閒適地問:「大郎可?是要去?」
張棹歌自然是要去的,她最愛湊熱鬧,不是,對傳統習俗最感興了,且多見識一些當地的活動,有助於?豐富她的大唐生活常識。
竇嬰仿佛早就看穿了她的本性,眉眼一彎,說:「我便不去湊這個熱鬧了,年年看也看膩了。但聽聞這是孟家牽頭辦的驅儺游神活動,七娘可?以去看看,只是別忘了帶上部曲、女使。」
突然被自家阿姊撇下,崔筠懵了一瞬,但很快就反應過來?這是一次很好的觀察孟家行事的機會,正好也可?以藉此機會拉近跟部曲、鄉民的關係,便點了點頭。
張棹歌本來?覺得這事跟自己沒?什麼關係,直到竇嬰再度把目光放在她的身上:「如此,還望大郎可?以幫忙護衛我家七娘一二。」
張棹歌難得遲疑了下,有些自作多情地想竇嬰是不是當月老之心未死。然而她跟崔筠的行程本就一樣,照拂崔筠也是順便的事,況且崔筠還會帶上僕從婢女,不是她倆單獨出門。
這麼一想,她瞬間就沒?負擔了,點頭應下:「行,順帶的事。」
崔筠的神色倒是如常,對竇嬰略帶小心機的安排也沒?有異議。
因為等會兒要出門,崔筠不能帶著一身炭烤羊排的味道?去參加驅儺,就先回到後院洗漱更衣。
張棹歌在等人?的時候,嚼了幾片薄荷葉去一去吃羊留下的膻味。
她眼角的餘光一瞥,發?現竇嬰將從她手裡?搶去的鵝形哨給綁在了灰兔脖子的紅繩上,像極了那些給寵物貓狗系鈴鐺的鏟屎官們。
張棹歌問:「你真打?算養著它?我看它挺肥的了,宰了做紅燒最好。」
竇嬰撫摸兔毛的動作一頓,看她的眼神充滿了無語,還有些防備,似乎真的擔心它被吃了。
「它比一般的野兔要乖巧,先養著吧。」
張棹歌剛想問一句兔子不臭麼,崔筠便已經洗漱更衣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