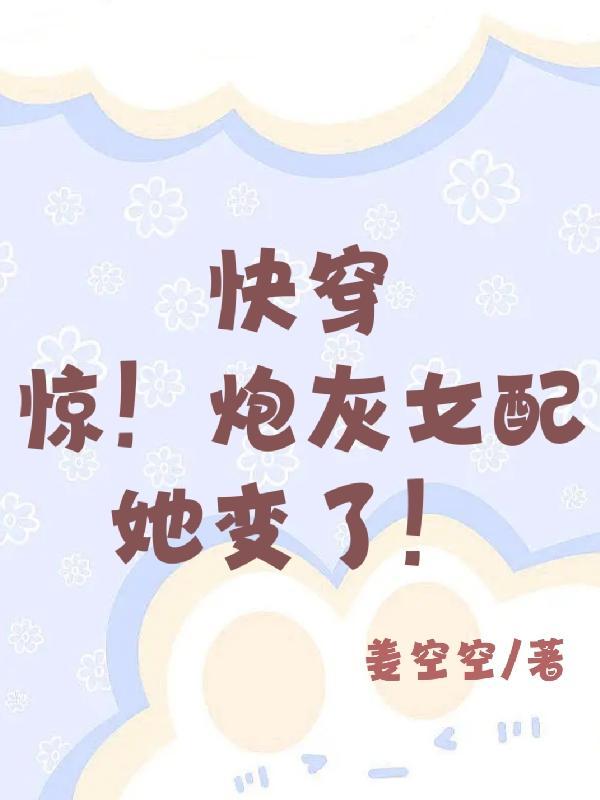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被招婿了 方便面君 笔趣阁 > 第76頁(第1页)
第76頁(第1页)
罷了,她又不髒。
張棹歌躺好後,問:「我明日有事做嗎?」
崔筠一噎,你自己有沒有事干,自己不清楚嗎?
她問:「棹歌想幫我做事嗎?」
張棹歌一聽,老?板要開始畫大餅了,說什麼都不能接茬。
她立馬說:「嗐,我也想,可邱斛和戚秧他們要回隋州,我得為他們踐行。」
「……」崔筠說:「需要用錢的話,可以去找夕嵐支一些?。」
張棹歌雖然不知道這場婚禮辦下?來具體花了多少錢,可看白天的宴席規模就知道開銷不小?。
況且牙兵是張棹歌找來的,自然該由她自己掏錢:「不必,我有錢。」
崔筠順著她的話問:「你哪兒來的錢?」
「上回王賀騁向我贖回他的馬給了我五兩金餅。」
張棹歌不提,崔筠都險些?忘了這事。
她心想,難怪這麼多人一旦沾了賭便再難戒掉,勤勤懇懇干一年活都不如在賭桌上贏一次,明知贏的機會渺茫,可為了那萬分之一的機會,也會拼一把,以致越陷越深。
張棹歌又說:「我本?想添作聘禮的,怎知這聘禮不會落入你的手?,我就收回來了。」
崔筠哭笑不得:「所以這就是你當初想以一匹絹作為聘禮的原因?」
雖說張棹歌出的聘禮都有崔筠報銷,杜秉騫也淘了不少好東西給她,可她不想便宜崔家人,就在聘書上寫了一匹絹。
崔筠發現後,才給改成粟三?十?六石、布二十?四匹。
這些?東西價值近八萬錢,但?與奪回那四五頃田所得的收益相比不算什麼,只要田地?經營得好,兩年內就能把這個錢掙回來。
「……」
兩人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很快就犯了困,再度睡去。
翌日一早,崔筠忍著困意?起來送走竇嬰的兄長竇大郎,及崔家安排的送親儐相。
隨後讓夕嵐帶人去將昨日未整理的賀禮、迎親抬的明面上的嫁妝等清理記錄在冊,自己則去算這次婚禮前後的帳目。
直到太陽西斜,朝煙來問:「娘子,已經酉時?,可要用飯了?」
崔筠恍惚地?看向西窗:「都這個時?辰了……大郎呢?」
「阿郎為諸位軍使踐行,剛回來。」
朝煙話剛落音,張棹歌的身影就出現在了門口處,探頭一問:「『阿郎』是指我嗎?」
朝煙無語,不然還能是誰?
張棹歌成了這個家名義上的男主人,崔筠自然也從小?主人升為女?主人,眾多奴婢僕役部曲對她們的稱呼自然得跟著改變。
張棹歌感覺自己解鎖了很多稱呼……儘管每個稱呼都槽點滿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