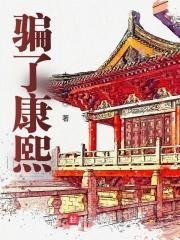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寤寐求之(双重生)讲的什么 > 57夫君(第1页)
57夫君(第1页)
貌美舞姬身段轻盈柔弱似柳,伴着微凉的晚风送来一阵旖旎的脂粉香,簇拥在一起,一道直直往正房去。
锦瑟原以为姜韫会坐视不管。
未料她蹙着眉瞧了几眼,而后徐徐起身移步至门前,冷声喝了句“拦着”
姜韫话音刚落,立时便有人上前去将那一行人拦住了。
领头的是幽州刺史的属官,见此不由吹鼻子瞪眼睛“太守赠予侯爷的贺礼,拦什么拦”
几个舞姬簇拥作一团,齐齐往适才出声之人瞧去,俱是一惊。
虽则那女郎素衣素钗面色苍白,神情难掩疲态,却依旧掩不住她夺目摄人的好颜色。她静静立在那儿,通身的气度和风姿便足以让人自惭形秽。
那属官在宴席上喝了些酒,有些醉意,眼下话出了口,才跟着侧头望了过去,顿时住了嘴,心里犯嘀咕这是从哪冒出来的貌美女郎难不成有人抢在太守前头巴结上了永平侯
姜韫面色沉静如水,丝毫不顾明里暗里的打量,淡声吩咐道“送客。”
府里的人先时未见主子话,听闻是奉幽州刺史之命送来的,便让人进了府,预备待得主子回府了再交由其处置。
眼下主母话了,自然便不敢再让人往里进了,连忙将人往外“请”。跟着沈煜出来的人,谁人不知这位夫人在自家主子心里的份量
自然是言听计从。
属官这才觉不对,有些急眼了。他离席前和太守拍着胸脯打了包票揽下了这活儿。本以为打着上峰的名号,将舞姬送过来便了事,哪想到如此横生枝节
这女郎分明端的是一副女主子的架势,永平侯的侍从和亲卫皆对她俯听命。
未等属官揣度出姜韫的身份,护卫们已然上前将人往外请了。
舞姬见这架势,连连后退,不情不愿地出府去。却有一个胆子大的,也是当中姿容最出众的那名舞姬,拈着帕子,横眉望向姜韫,目光中带着几分挑衅。
“妾几个是奉太守命,来伺候侯爷的,侯爷和太守未话,旁人哪能随意置喙我等去留”那舞姬遥遥盯着厅前所立的女郎,语气轻柔,话里话外却不客气。
“是这个理”那属官闻言,跟着附和道,“便是要将人送回去,也待侯爷回来了再定夺才是。这位夫人您也不必冒险担责替侯爷拿主意不是”
姜韫脸色冷了下去,懒得再同这些人纠缠,正欲以眼神示意侍卫们动手送客。恰在这时,忽闻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紧接着便是数人交错着的脚步声。
众人闻声,齐齐往府门前望过去,便见永平侯沈煜带着几名亲兵御马回府了。
沈煜本就无意在战时捯饬什么庆功宴,偏那幽州刺史李晟几次三番着人邀约,适才在席上听闻姜韫人已至幽州的消息,几近坐不住,耐着性子推杯换盏了几个回合,便急急告辞离席了。
眼下他快步进府,一打眼瞧见府中这情景,眉心顿时紧拧。
才刚李晟在席上便想将这几个舞姬塞给他,被他一口回绝了,谁想竟连个招呼也不打,直接将人送到他落脚的府里来了。还好巧不巧地正撞上了行至幽州的姜韫。
李晟那竖子,净给他添堵
众人见正主回来了,一时间皆沉默下来,按兵不动。
姜韫掀起眼皮子望向沈煜,轻抿了下唇,而后往他身后望去。
未料并未瞧见姜韬。
她当下便皱了眉,忍了忍才未立时移步过去质问。
沈煜见她神情不愉,眼皮跳了几下,沉下脸快刀斩乱麻,拎着李晟那属官的衣领,将人丢了出去。
“滚”
那属官一下子被拎起来了,吓了一跳,回过神来,忙不迭道“侯爷下官是奉太守之命”
沈煜抬腿踢了他一脚,冷声警告“你去告知李晟,如若再有此等事,他头上那顶官帽我亲手给他摘下来。”
那属官痛呼一声,跌坐在地上,一抬眼见永平侯阎王似的扶刀立在那儿,一身凌厉之气骇人得很,不禁往后缩了缩,回过神又忙不迭爬起来应下。
那几名舞姬见此,皆惊恐连连,觑着永平侯的身影,半是遗憾半是惧怕。府里的护卫们这时又在沈煜的示意之下,上前将她们送出府去。
几人拈着帕子,含羞带泪地鱼贯而出。先时出言的那个,到底心有不甘,几次三番望向永平侯。凭她的姿容,把握住机会,做个侯府的妾室,
往后的日子便有了着落。
奈何永平侯半分瞧她一眼的意思也无,身姿笔挺地立在门前,正欲转身进府。
那舞姬盯准了时机,在永平侯与她擦身而过之时,脚下一软,直直往他的怀里跌过去。
却未料沈煜只侧眸瞥了她一眼,又收回了目光,往旁侧避了一下。
她难以置信,弱柳扶风摇摇欲坠之时,被一只纤细柔荑从身后扶了一把。
姜韫抬手将人扶起来了,面无表情地道“这般想留在这儿”
那舞姬咬了咬唇,眼眶微红,委屈得很。
沈煜面色沉沉,目光紧盯着姜韫。
姜韫见那舞姬我见犹怜的模样,忽然轻笑了一声,淡声道“既然我无权置喙你的去留,你问他便是了。”
那舞姬闻言,面色顿时青白交加。适才永平侯动怒的样子,众人皆瞧得一清二楚,意思分明得很。她最后使了点心眼想搏一搏,谁料永平侯竟如此不解风情,温香软玉避之不及。
何必再问自取其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