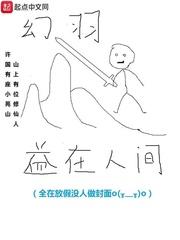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三月的快穿之丁岚 > 第69章 戏子多情(第1页)
第69章 戏子多情(第1页)
李三月留意起了满堂彩出入的人员,那个曾服务过一次的,黑色长衫先生,每个礼拜,必有一天来这里喝茶。而他来的那天,必定是梆子戏《大登殿》,旦角小凤凰登台的时候。有时候一场戏唱完,还会邀请小凤凰去7号包厢一叙。
也许他爱听小凤凰的戏?
李三月靠在大堂内栏杆边,肩膀上搭着一条布巾,若有所思地看着小凤凰从7号包厢出来。
唱戏的人行走时,脚步,肩膀,手,都自有一股仪态,看起来分外悦目。
小凤凰是个才18岁的女孩,乱世没有孩子,就凭着她能坐稳戏班子台柱一角,就知道不简单。
“跑堂的,看什么呢你?春猫子叫,起了心思了?”小凤凰还没卸妆,依旧是戏中王宝钏的装扮,看起来明眸皓齿,灵气逼人。
“7号包厢的先生,很是捧你场。经常看见。”李三月好像是随口一说。
小凤凰也无所谓一般拿起帕子沾了下朱唇,扬起一抹笑。
“任他再是什么草莽英雄,贩夫走卒,哪个看过我小凤凰的戏后,还能忍住不来第二趟?就连你,不也常常在台下,睁着那双招子,转也不转?”
“是了。”
李三月微微点头,不否认,而后看到一桌客人招手,便从小凤凰身边走开了。
两人擦肩而过时,谁都没有看谁,好似一切都是随口一说,闲聊而已。
李三月在等待着,他有预感,会有人找上自己。
又过了半个月,这座老城里,日本兵越来越多了,大街上路人减少,好像日本兵在抓什么人一样,胆子小的商户直接闭门歇业,李三月照常去满堂彩上工,只是这天夜里十点多回家时,在居民区那些杂七杂八的棚子下,遇到了一个躺在阴影里的男人。
李三月本想一走了之,谁知身后就传来日本兵说话的声音,与这处只差一堵墙,转弯就能看到。联系到最近不一样的风声,李三月心思一沉,决定赌一把。他将男人扶了起来,几步离开此处,回了自己租住的阁楼。
隔壁灯已经灭了,那对年轻夫妻不知道在不在家。李三月不敢弄出太大动静,只是把捡到的男人放在床上,点燃了煤油灯。
灯光下,是李三月有过一面之缘的灰色长衫先生!
男人看起来文质彬彬,戴着眼镜,浑身没有什么肌肉,很是瘦弱。腹部一处血迹明显,打湿了身上的灰色长衫。
李三月伸手解开对方衣服,看到了对方腹部有一处枪伤,索幸子弹是穿过了皮肉,只是伤口流血严重。他拿出自己空间里的医药箱,擦完伤口,撒上云南白药,用纱布包扎起来,男人皱着眉头,只是都没醒来。
当夜,李三月在地板上打了地铺,早上又给男人留了一碗清水,一个窝窝头,一个水煮蛋,才去满堂彩上工。
白天一整天李三月都心不在焉,后厨厨师长比较喜欢他,今天给他偷偷留了半个猪脚,李三月用油纸包了起来,带回了家。
他走到阁楼门口,有些忐忑,直到打开房门现空无一人,说不清是失望还是理所应当。桌上给男人留的早餐已经被吃了。李三月愤懑的自己坐在桌子前,把猪脚啃完了。
日子又恢复平静,李三月自从上次和小凤凰对话过后,再也没有看见过黑衫先生来这里喝茶看戏。小凤凰照旧在台子上唱着“王宝钏低头用目看,代战女打扮似天仙。怪不得儿夫他不回转,竟被她缠住一十八年……”
年关将近,李三月来到冀中已经一年。逐渐习惯了这里的胡辣汤,馍馍,面条等。闲暇时他也曾坐在台下,眼睛看着小凤凰,心思飘到了远方。
戏班子过年是最忙的,官员府邸,富商家里,日本兵营里……哪里给钱,就去哪里唱,班主赚了个盆满钵满,小凤凰脾气也一天天见大。
李三月曾经看到她不唱戏时,坐在后院里,脸上没有那些脂阿粉阿的,穿着旗袍,嘴里叼着烟,却好像有心事一样,歪着头,翘着腿,不言不语,只是抽烟。有时候她脸上会有乌青,旗袍底下露出的皮肉上,有割伤,有烟头烫伤等一些乱七八糟的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