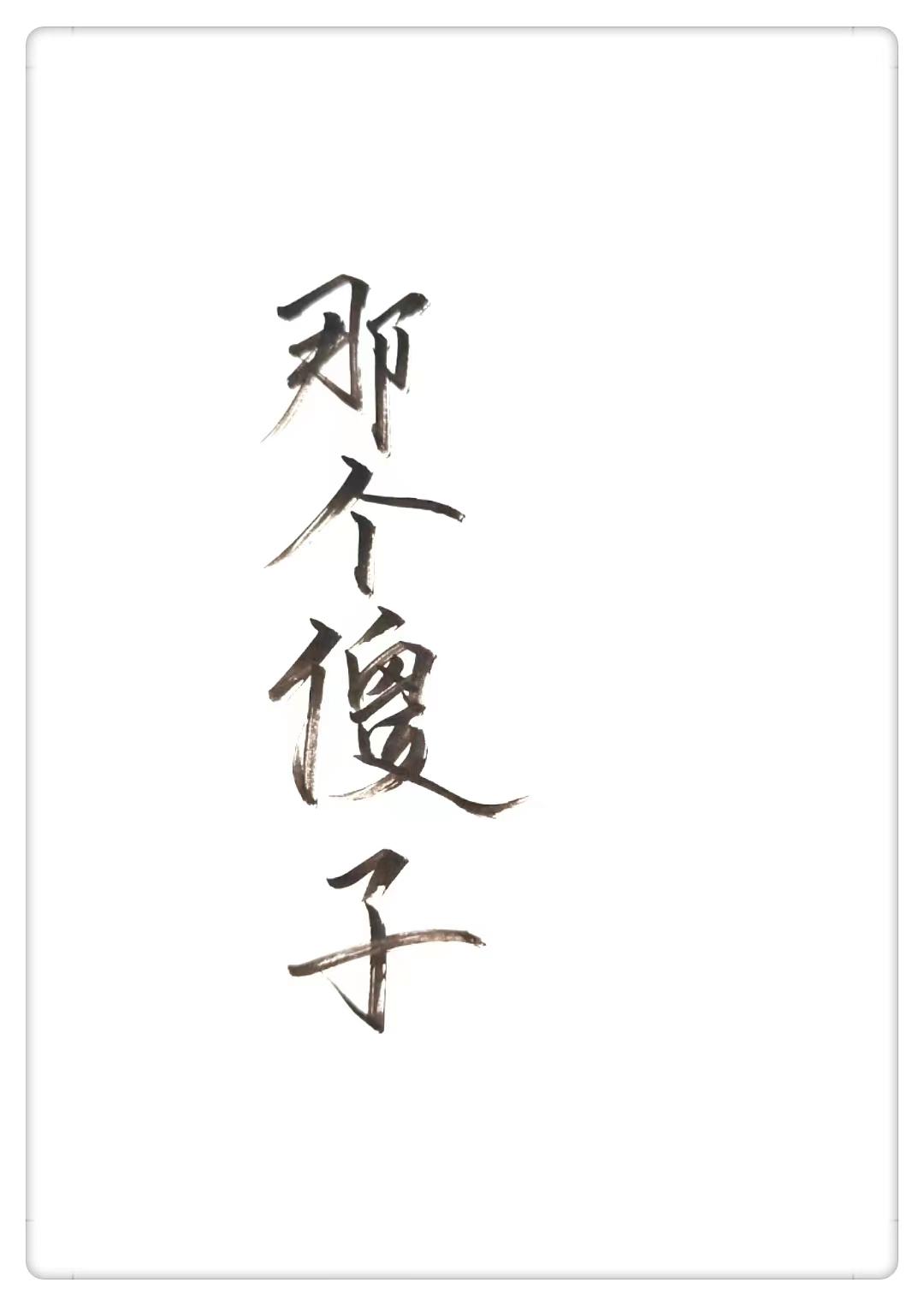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侯夫人只和离不原谅 > 第61章 下次不知夫人要拿什么来换(第1页)
第61章 下次不知夫人要拿什么来换(第1页)
茶楼厢房内,茶香袅袅,阳光透过雕花窗棂洒在二人身上。
萧慕止听完赵书晴的话,微微挑眉,身体往后靠了靠,一只手搭在椅背,姿态慵懒,嘴角噙着一抹若有若无的浅笑,静静等着赵书晴下文。
“我要沈梦行回来。”沈梦行乃是明王嫡子行事风格狠厉,却不似其父那般变态,最主要是,沈梦行曾欠她一条命。
她要沈梦行回来护着秦文心!
如今沈梦行不在京城,赵书晴手中无人,无法寻到他。
萧慕止舌尖顶了顶腮帮,“夫人倒是热心肠,此前为那曲家姑娘操心,如今又要管这事儿。怎么,不做夫人,倒想做那慈悲为怀的活菩萨?”
赵书晴先是一笑,而后她缓缓倾身,靠近萧慕止,那双杏眸眼里皆是坚韧,红唇轻启:“要你管。”
一阵风从窗户吹进厢房内,吹起桌面上账本纸张,发出沙沙声响,静默片刻,萧慕止骤然哈哈大笑起来
这一笑,打破了剑拔弩张的寂静,也让赵书晴身后的兰儿松了一口气。
她真怕自家小姐惹恼这位杀神。
萧慕止一只手放在桌面上轻轻敲着,哒哒哒的声音一下又一下落在人的心头上。
反观是赵书晴不疾不徐,坐姿优雅端庄,浅浅品着茶。
“行!”这是萧慕止的回答。
赵书晴把剑谱放在桌子上,推给萧慕止:“王爷,您的东西。”
萧慕止轻轻扫了一眼,并没有直接去拿,反而倾身上前,“侯夫人的处境不是很好啊,如此涉险与我交易,无异于与虎谋皮。”
赵书晴伸手把他桌面上凉的茶水倒了,给他倒了一杯新的,“能说出这样的话,想来王爷并非无情之人。王爷与兄长交情颇深,想必也不会忍心看旧友妹妹深陷险境。”
萧慕止拿起剑谱:“这本剑谱,我就收下。下次,不知夫人要拿什么来换。”语毕起身欲走。
“王爷,我这里还有一幅兄长字画,还想请你帮个小忙。”
萧慕止闻言,脚步稍滞,侧眸看着赵书晴,阳光把她整个人都照得十分柔和:“姑且说来听听。”
一刻钟后,萧慕止离开后,赵书晴微微叹了口气,手指无意识地在茶杯边缘摩挲着,不知方才萧慕止承诺的事情,会进展如何,她万不能让二哥受到这等侮辱!
这时,兰儿贴心地换了杯新茶,轻声的询问将她从思绪中拉回:“小姐,大少爷似乎从未留下字画?”到时候,哪里来的字画给萧王爷啊?
赵书晴闻言抬眸看向兰儿,眼底皆是狡黠的笑意:“留了,怎么没留。我留了就是留了。”萧慕止又不住在赵府,他怎么会知道赵承煜有没有留字画!
“那到时候我们拿什么给萧王爷……”兰儿刚想问出口,突然想到小姐的字与画都是大少爷教的,且神韵颇似,难不成小姐打算……想到此处,她忽然间捂住嘴巴。
赵书晴喝尽茶水,把茶杯搁置在桌面上,兰儿忙取过披风,替赵书晴系上。
二人沉默片刻,兰儿看着赵书晴,忍不住又问:“小姐,为什么萧王爷会如此执着大少爷所留下的物品?”
赵书晴其实也疑惑,哪怕兄长与他是故交,但,按照她对兄长的了解,这二人想来交情也是一般。
“谁知道。”只要他愿意收,能帮忙,有些事情何至于深究呢。
赵书晴推开厢房离开茶楼了。
此时,上完早朝的沈策州,心事重重地借故来到御书房。
御书房内,龙涎香的气息萦绕在空气中,沈策州鼓足勇气把赵承弼借阴婚冲喜一事提了一嘴。
新皇原本批改奏折的手一顿,抬头,满脸诧异:“你说什么?”
沈策州深知新皇对赵家心存忌惮与不满,心中略有紧张,但话已出口,他硬着头皮,再次上前,躬身道:“圣上,赵承弼虽犯下重罪,但念及其兄赵承煜曾为我朝立下赫赫战功。如今赵承弼在狱中病情严重,恐不久于人世。民间素有阴婚冲喜之说,虽无依据,但或许能给赵家人一丝慰藉,也彰显圣上对功臣之后的体恤之情。”
新皇眉头紧皱,视线落在沈策州的身上,满是探究。他微微沉吟,眼底倒是露出几分兴味:“阴婚?冲喜?”
然而,如此荒唐的提议,新皇并未动怒。沈策州见状,暗暗松了一口气。
新皇把朱笔一丢,站起身来:“今日朝堂上,你因外祖家一事,遭到御史们的轮番指责,转手把这事推给了赵家。你就不怕,朕允了,更加引起御史们的抗议与谩骂?”
沈策州躬身更低,“臣提出此意,绝无私心,只是念在家中夫人,所以……”
新皇抬手制止沈策州的话:“冠冕堂皇的话就别说了,容朕考虑一番。”
新皇让沈策州近日做事稳妥一些,切勿再让御史抓住把柄,沈策州连连称是,便退了下去。
沈策州一走,太监总管安公公上前,低声询问:“圣上,侯爷此计不妥,若是圣上允了,想必会遭受御史口诛笔伐。”
新皇半眯着眼睛,沈策州一走,太监总管安公公上前,低声询问:“圣上,侯爷此计不妥,若是圣上允了,想必会遭受御史们的口诛笔伐。”
新皇嘴角浮起一丝冷笑,眼中闪过一抹厌烦:“哼,朕岂会不知这其中利害?那赵承煜,活着的时候就处处与朕作对,全然不将朕放在眼里。如今他虽死,朕对赵家的厌恶可丝毫未减。”
新皇微微眯起眼睛,踱步沉思片刻,接着说道:“不过,朕如今根基未稳,不能与御史明着来。此事借着朱家由头办,你去告知沈策州,让京兆府府尹暗中配合,不许泄露半分!”
就在安公公着手刚告知沈策州时,沈策州嘴角的笑还未扬起,便有下人匆忙来报:“侯爷,侯爷不好了,朱家老爷被,被林氏杀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