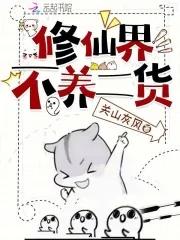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犯上娱乐圈在线阅读 > 第103頁(第1页)
第103頁(第1页)
杜葉青有些吃驚地微微睜大了眼看著陳墨低落的側臉,張了張嘴,沒說出話來。兩人想著各自的心事,沉默了很久,杜葉青放鬆下自己僵硬的肩膀,歪過來靠在了陳墨的身上,道:「我大概懂了一點……不說了,睡一會。"
接近十小時漫長的飛行,杜葉青靠著陳墨睡了一會,醒來之後發現陳墨安靜地低著頭,劉海遮著眼睛,動作僵硬地閉著眼。他小心地動了動,讓陳墨靠上自己的肩膀,手指有一下沒一下地從他的髮絲間穿過。夜間航班上一片寂靜,陳墨淺淺地呼吸從他耳邊划過,在萬里高空之上帶著一種能夠穿越時空的力量,讓杜葉青心中一片寧靜。暫時拂去兩人之間陳年的誤會和陌生感,他漂泊了五年的心好像終於落到了實處,打心底開始有了溫度。
飛機在斯德哥爾摩著地的時候,當地時間是凌晨三點。兩人在機場不遠的酒店休息了一會,早上九點的時候一起在陽光明媚的咖啡館裡吃了早餐。杜葉青只說要帶陳墨去一個地方,飛了這麼久,陳墨也沒有問目的地是什麼,杜葉青也沒有直接說出來。吃過早餐之後,杜葉青看起來並不著急,像個普通的旅客一樣在公園裡餵鴿子。
正值休息日,公園裡人很多,尤其是追追打打的小孩子。杜葉青和陳墨並排坐在噴泉邊的長椅上,十數隻鴿子圍在他們腳邊,忙碌地啄著杜葉青撒下的穀粒。明媚但不燥熱的陽光從天空中流瀉而下,穿過鬱鬱蔥蔥的梧桐樹,在地上和他們身上灑下溫柔的斑駁。杜葉青低頭看鴿子,陳墨偏頭看他,有一個背著單反的中年從他們前面經過,忍不住停下來,把這一幕拍進了相機里。
「時間停下就好了,」陳墨輕聲說,「像做夢一樣。」
「那這個夢要做很久了,」杜葉青嘴角微微上翹,「等到我們都老了,可以整天整天地像這樣無所事事地坐在一起,喂喂鴿子,做做夢。」
陳墨和他緊緊地十指相扣,扣得指關節發白。杜葉青低下頭,安靜地看著鴿子們吃完了所有的穀粒,用另一隻手拍了拍身上的碎屑,站起來,拉住神色還有些恍惚的陳墨,道:「走吧。」
兩人輕裝上陣,只有杜葉青背了一個不大的背包,在路邊隨便找了一家牛排店吃過午餐之後,計程車轉公交車轉巴士,一直從艷陽高照坐到斜陽沉沉的時候,離開了相對繁華的市區,進入了一個人煙稀少很多的小鎮。巴士里加上他們只有六個旅客,車站也冷清清的,下車之後前後都是一片綠油油的小山丘,整個視線之內只有兩戶人家。杜葉青在車站裡拿了地圖,走了接近四十來分鐘,有一個小小的湖出現在他們面前。
湖邊零零散散地種了十來棵樹,附近的幾塊地被開墾了出來,種了一些花花草草和作物。有一棟不怎麼起眼的木屋依湖而建,大約有三層,沒有使用任何鮮艷的油漆,乍一看幾乎要和天、地、湖融為一體。
他們走得近了,木屋的很多細節進入了視線之內:陰涼愜意的藤蔓架、做工精良的銅質鞦韆、被鮮花環簇懸在二樓的小陽台……陳墨的視線往右移的時候,看見一個中年男人正拿著剪刀在小花園裡修剪花草,穿著非常隨意的背心和短褲,一張典型的西方人的臉,對於在娛樂圈裡看慣了俊男美女的他來說算不上大帥哥,五官和身材也挑不出大的刺來。杜葉青很快也注意到了他,慢慢停下了自己的腳步,神色還是平和的,只安靜地、認真地看著那個人的臉,看痴了一樣,足足三四分鐘沒有動靜。
陳墨碰了碰他的手背:「朋友?」
杜葉青被他碰得整個人都縮了一下,轉過頭來。陳墨有些吃驚,皺起眉看著他發紅的眼角:「怎麼了?」
杜葉青笑了起來,表情說不出是高興還是難過,或許更像這兩種感情交融之後的神色,聲音有些啞啞的,道:「沒什麼,我去打個招呼。」
他大步朝著專心修剪花草的男人走過去,站在小小的花園的邊緣,用英語朝著男人打了聲招呼。男人抬起頭來打量他們,沖他們溫和禮貌地笑了笑,視線很快就落在了杜葉青身上,用流暢的英語回問:「兩位都是亞洲人吧,是B1anche的朋友?」
杜葉青道:「是的,她在家嗎?」
「很快就回來了,」男人看起來似乎很高興,馬上放下了剪刀,帶他們往木屋走,「先進來坐一會,一路找過來恐怕很累了。」
三人一齊進到了客廳裡面。從外面看著只是樸素的木屋,裡面卻出乎意料裝修得非常精良,遠遠比想像中的要寬,比起杜葉青在J市的別墅來更加寬敞精緻,且多了幾分生活的味道。男人進廚房給他們泡茶,杜葉青和陳墨並肩坐在沙發上,目光一寸一寸地打量客廳里的擺設,整個人都有些愣愣的,瞳孔發沉,像是在打量,又好像透過了這些東西在看什麼別的。
男人為他們泡了花茶,端出了茶點和鮮的水果,在他們對面的沙發上坐了下來,視線依然是落在杜葉青身上的,有些拘謹的樣子,沒有說話,只衝著他笑,一邊笑一邊含蓄地打量著他。杜葉青正要開口說點什麼的時候,外面傳來了門鈴的聲音。
陳墨感覺到杜葉青的身體一下子就繃緊了,男人也迅從沙發上站了起來,道:「她回來了!」
男人去門口開門,杜葉青反而把頭垂了下去,渾身僵直,緊張地盯著自己的手背。門口隱約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用瑞典語和男人輕快地交談了幾句什麼,然後聲音戛然而止,緊接著是一陣羽毛般輕的腳步聲,一直停在了他們不遠的地方。
![[武周]问鼎](/img/22977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