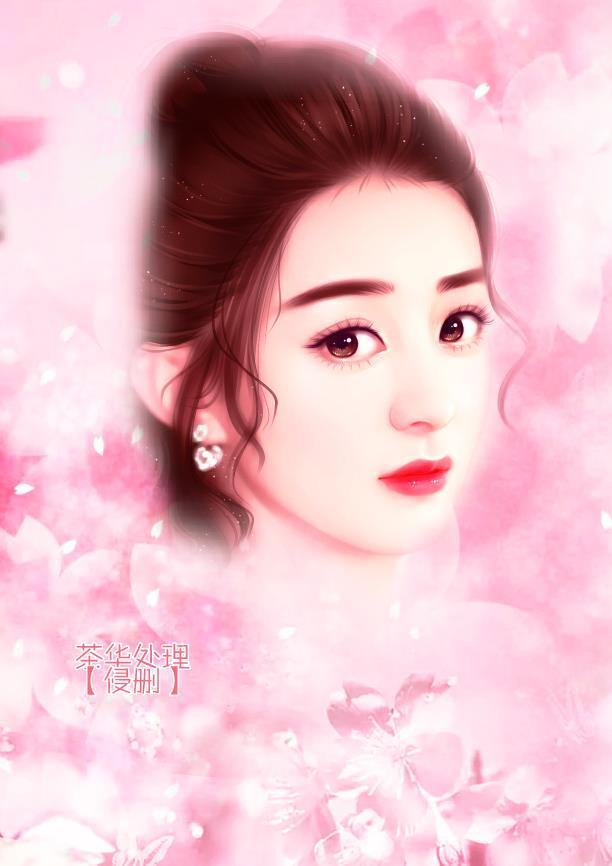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拜皇上打一数字 > 第33章(第1页)
第33章(第1页)
「青冥……」
梅砚的心狠狠疼了一把,抚上宋澜的额头,竟觉得烫手。
廖华已经跟进来,又要拦梅砚:「梅少傅,这病实在容易过人,有卑职和太医侍奉便好,您快些出去吧。」
梅砚半晌没说话。
廖华以为他不知暑热病的厉害,又絮絮叨叨地说:「这病得上了便要发热,高烧不退,人也醒不过来,太医已经换过好几幅药了,可是不仅陛下不见好,还有几个宫人陆续染了病,梅少傅,您万万不要小瞧了这病的。」
「我知道。」梅砚轻声说。
廖华抿了抿唇,「您知道?」
「嗯。」梅砚说着在宋澜身侧坐下来,抬手取了床头上晾着的帕子去为他擦汗,一边道,「我幼时在盛京城住过,那时也见过这病。」
廖华没想到他会这麽说,只得道:「您既然知道这病,就莫要再呆在这屋里了,陛下千叮咛万嘱咐过的,您若是有个好歹,卑职如何交代啊。」
梅砚不为所动,而是抬眼看了看屋里那几个蒙着面巾的宫人,缓缓说:「我就在这里照顾他,也会按时服药,及时沐浴净手,你别再劝了。」
隔了这麽久,他终於说出了那句话,那句宋澜苦苦恳求了多时的话。
——「我不走。」
廖华攥了攥拳,已经看出来自己劝不动梅砚,便退下去嘱咐太医,屋里一时静了下去。
梅砚吩咐那几个宫人出去烧水,又让人准备乾净的里衣,他们乐得自在,忙不迭都退了出去。
时节已至芒种,天气暑热,今天又似乎比往日更热,外头的芍药花都晒蔫了,屋里的安神香徐徐燃着,瑞脑销金,似乎给人添了几分烦躁。
梅砚用手上的帕子为宋澜拭去了额头上的汗,轻轻拨开他脸上的碎发,便露出来一张俊朗非凡的面容,羽扇一样的睫毛阖在眼睑上,因着发热的缘故,嘴唇也泛着明艳的红。
屋里静得出奇,梅砚一时在床前怔怔坐着,竟觉得有些心乱如麻。
从他孤身来到盛京城,染翰成章,写下那些锦绣文章开始,他就从没有过这般心神不定的时候。
他越过青骢马,跻身朝臣殿,蛰伏东宫五载,搅动朝堂风云,没有一刻慌乱过。
他搬倒徐玉璋,逼死先帝,被宋澜软禁在癯仙榭里整整一年,也没有怕过。
即便是他为平宋澜滔天的恨意而甘心委身於床帐之上,也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恍惚。
那是他一贯冷静的意志,可如今的心里乱成一团,这又是什麽?
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写书的人,忽然不知道该怎麽写了,就只能一个人乾巴巴地坐着,细细捋着故事的主人公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却发现无论是误会也好,隐瞒也好,此时此刻都显得不那麽重要了,唯有眼前的人。
唯有眼前的人。
小宫女担惊受怕地把梅砚要的热水和里衣送进来,梅砚嫌她们碍事,又摆了摆手让人出去。
梅砚把宽大的袖子挽起来,拿了帕子去盆里洗净,而後轻手轻脚地解开了宋澜身上的寝衣。
天很热,但宋澜的身体太虚,屋里没放冰,他也只盖了一层薄薄的被子。梅砚将他的寝衣放在一旁,伸手捏了捏那被子,觉得被子也有些湿汗。
宋澜实在是出了太多的汗,才被擦过的额头又隐隐有了汗珠,他应当是很难受的,被梅砚翻动的时候还有些抗拒,眉头紧紧皱着。
梅砚细心地给他擦身上的汗。
一寸一寸,指尖垫着绢帕,碰上宋澜结实的胸膛,白皙的肌肤,梅砚心里微微颤了一下,而後又不动声色地擦过去。
梅砚年少时也是世家出身,身份贵重,不曾做过伺候人的事。後来家遭变故,在钱塘的那些年磨去了他年少时候的那些骄矜与自傲,让他放下了身段与过往。
母亲过世的时候,兄长也曾大病一场,他也曾这样细心照料,只盼着天一亮,像梦一样的世事就可以醒过来,醒来以後依旧是春衫少年郎,阖家满一堂。
就这般心神不定地为宋澜擦洗过,又给他穿上新的里衣,梅砚没再麻烦那些怕得要死的宫人,而是亲自去橱柜里找了一床薄被给宋澜盖上。
梅砚的法子是有效的,这麽一会儿功夫,宋澜的脸色已经好了许多,只是烧并没有退下去,额头烫得厉害。
他想起自己不久前生的那场病,应当也是这样发热的。
梅砚轻轻笑了笑,又拨了拨宋澜的头发,看着那个昏昏沉沉睡着的小皇帝,像是喃喃自语:「我方病罢你登场,这算个什麽事儿。」
「咚咚」两下敲门声,廖华送了药过来。
「梅少傅,您歇一歇,卑职来喂陛下用药吧。」
梅砚没应,见他端着的是两碗苦黑的汤药,稍稍定了定心。
「还是我来吧,晚些时候我会去沐浴,此时不差这碗药的事儿。」
廖华没强求,看得出来梅砚是铁了心要亲自照顾陛下,便又退出去为梅砚准备沐浴的事情,心中想着万万不能让梅少傅也染上病。
不然陛下会杀了他。
梅砚端过其中一碗汤药,放在嘴边轻轻吹了会儿,待药温了才干巴巴地唤宋澜,「能听见吗,青冥,起来喝药了。」
宋澜都快烧死过去了,自然是听不见。
梅砚别无他法,只取了半勺的药,续到宋澜嘴边,这一次宋澜有反应了,他睡梦里意识到这是苦涩的味道,舌头卷了卷,把药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