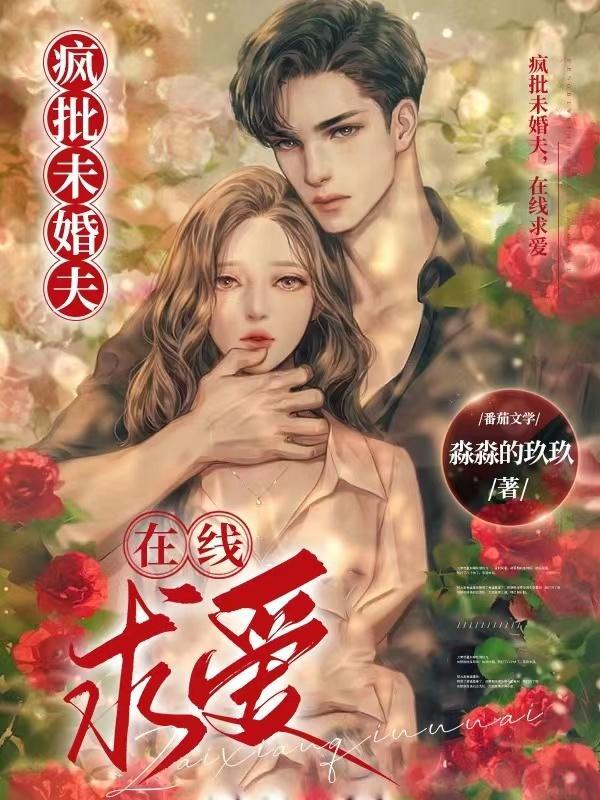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虐主文的npc消极怠工了 > 第457章(第3页)
第457章(第3页)
这是张足够出众的脸,脸颊因热泛着薄粉,也是他如今,唯一的本钱。
等确定没有问题,梁叙换上簇新的睡袍,系带松松垮垮,睡袍刚好露出脚踝,行动间能隐约看见修长笔指的小腿,他刻意没穿拖鞋,也没贴信息素贴,就那么拧开门,赤脚走了出来。
时律正在整理被子。
客卧平常不睡人,被子收在衣柜里,需要拿出来铺好。
他听见动响,转身看见梁叙,对方赤脚踩在地板上,没有擦头,任由水珠从碎上滚落下来,濡湿了脊背大片的衣料。
接着,青竹酒的幽冷的气味从他呼吸中、丝间和皮肤下里逸散出来,整个卧室似乎都被这酒香浸透了。
梁叙抬眼看他:“时总……我……”
他正想着该用什么样的人设,是故作矜持,假装懵懂,还是更加直白的勾引,却见时律垂眸,有点狼狈的移开视线:“你……稍等,我去拿腺体贴。”
梁叙来不及阻止,时律就抬手调高了地暖和空调的温度,而后哐当一下夺门而出,找到腺体贴,将梁叙扯过来,撩开他的头,啪唧一下扣在他的后颈,又不知从哪拽来毛巾,劈头盖脸的丢在了梁叙的脑门上。
梁叙:“……”
视线被毛茸茸的毛巾遮挡,梁叙很轻的眨眼,时律已经动作起来,将头擦的半干,而后才掀开被子,命令道:“你进去。”
梁叙不明所以,依言钻进被窝,茫然的抬眼看时律,狐狸眼中的笑意散尽了,有些儿呆,而时律扣着他的肩膀将他按进被子里:“睡觉,好晚了,不睡觉长不高。”
梁叙心说他早过了长高的年纪,却无法抵抗时律的重压,被连人带被打包成卷儿,最后时律啪的一关灯:“晚安。”
“……”
眼见时律抬步离开,真的要走,梁叙连忙:“诶,时总!”
时律回头:“嗯?”
“……”
梁叙抿唇,如果说刚刚衣衫半透,他自诩有几分姿色,现在一条长卷,就只剩下搞笑了,于是呐呐良久,闷声道:“……晚安。”
时律离开了。
老婆虽然不在怀里,但乖乖待在家里,主卧次卧几步远,时律非常满足,睡得也十分安稳。
他不知道的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梁叙没睡,而是悄悄起床,在房中转了一圈。
他扫过洗漱台,只有一份洗漱用具,看过餐厅客厅,没有第二个人的痕迹,又打开鞋柜,只有一个尺码的鞋。
从种种蛛丝马迹中判断,这房子没有第二个主人,那位时总,确实是独居的。
梁叙悄然松了口气。
从时律将他带回家,以及之后的一系列动作来看,至少目前,时律挺喜欢他,甚至可以说是……珍视。
梁叙不明白这珍视从何而来,但他希望更久一些。
抱着这样的心思,梁叙回到了客卧。
他定了个明早六点半的闹钟,准备起床给时律做早饭。
时间已经走到两点,还有四个多小时睡觉,梁叙关了手机,有点烦躁。
他不喜欢早起,更不喜欢熬夜后早起,这会让他皮肤暗淡,失去最后的本钱,但作为有求于人的omega,梁叙觉得自己有必要展现乖顺与贤良淑德的一面。
于是第二天闹钟一响,梁叙就像台精密的仪器,瞬间进入了状态,他穿好衣服,推门走到厨房,回忆着宴会上时律的口味,正思考做些什么能既不太过刻意谄媚,又能让时总吃的舒心,一抬眼,却是愣住了。
那位身价高到足够令叶老爷子忌惮的时总,居然已经起了,正在灶台边捣鼓着牛奶和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