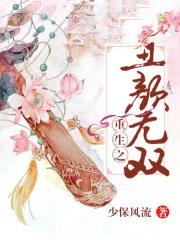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创造一个角色的关键点是什么 > 何谓观众(第1页)
何谓观众(第1页)
何谓观众?
有什么能比我们的童年更美好?在人类生活的这一阶段,整个世界似乎都是一个巨大的谜语;万事万物都充满了神秘;稚气的童心在一个机械玩具面前热切地怦怦直跳,一门心思地要找出这个玩具里究竟隐藏了什么——全部生命似乎都聚焦到这两个问题上:它是什么?还有,为什么?——在这一阶段,生活中没有其他的问题存在,只有“认识”和“理解”。
但是,随着年纪渐长,留待我们发现的东西越来越少——我们的玩具的秘密大多已被揭穿,我们对于大多数“为什么”都有了现成的答案。换言之,我们的生活进入了应对日常问题易如反掌的阶段,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不再是谜语,而在很久以前就被彻底地处理与破解了。
然而,我们天性中的神圣火花是如此强劲,我们无法就此止步,满足于我们已经一目了然、已经揭开谜底的事物;我们如孩童一般,继续寻找新的可能性,以期对阵另一个谜题,在我们心里再次激发那个永恒的问题“为什么”——这种追问,指向比往昔或者当下更美好的事物,会帮助我们实现对尽善尽美、对理想的持之以恒的求索。
为此,人类就像渴望新玩具的孩子一样,把生命投入科学研究中,为全面认知上帝而创立新的教派,用艺术品来装饰自己的生活,并对戏剧保有一种天真的不过
几乎是无意识的热爱——在戏剧中,世间奥秘被光华灿烂地展示出来,生活显得如此美丽、如此诱人,与真实的生活判若霄壤。
戏剧观众无非也是拿到新玩具的孩童。一个孩子的所有情感,或者一个未开化的野人目睹现代发明创新时的感受,你都能够在聚集到剧院里的人心中找到。不妨在演出开始前盯着观众注目片刻——多么生气勃勃的面孔!多么热切的期待!然后,“嘘”的声音会穿过观众席,那是他们提醒彼此注意幕布正在徐徐升起。如果演出真正具有创造性,观众的情绪会越来越激昂;如果在表演接近尾声时,这股劲头松懈下来,让位于不满与厌倦,那也不能怪罪观众——它仅仅意味着这一次戏剧未能揭晓谜底,没有回答孩子的问题:“玩具里面有什么?”
你是否注意到,大多数人在告诉朋友自己晚上要去观看一场首演时,都是一副郑重其事的神气?听起来简直就像一个人声明“今晚我将要成为父亲!”一样庄严。我不知道有谁(也许戏剧评论家是个例外)是勉为其难地去看首演的。即便上次扫兴而归——很不幸,这种情形并不罕见——也无法抹杀他对观看新戏的殷殷期望。这就是为什么戏剧在首演之夜总能找到观众。至于随后的演出是否有人观看,则完全取决于剧本、演员和整个剧团了。
戏剧观众有一种不同
寻常的孩子般的信赖感。他几乎总是盲目地为一部未知的戏慷慨解囊,坚信他喜爱的剧作家、演员或者制作人不会令他失望。我敢说你不会未经试穿就买一双鞋,哪怕是名牌精制。看看有多少荒唐之处被公众宽宏大量地放过不提了:
摇摇晃晃的石墙。
一缕月光追着主角们满台乱跑。
无知的台词!
与演员的身量和地板上的树木相比,房屋看起来小得离谱。
恋人们把含情脉脉的表白扯着嗓子喊出来,声音大得足以把所有邻居都招来。
村姑穿着丝制格纹裙,戴着大串钻石项链。
咆哮的反派角色除了深仇大恨之外,不晓得还有其他情感存在。
危险近在咫尺,私奔的情侣还非得说上好几页对白。
酒杯晃来晃去,里面的酒却一滴不洒,依然满至杯口,违背所有自然法则。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样的荒唐事成百上千,即使首屈一指的商业剧院也在所难免。所有这些,观众都心甘情愿地容忍了,只要在演出中有些微的真实,有人类一直渴望的“高于现实”的生活的隐约微尘。
当红演员所受的膜拜又该怎么说呢?演员所得的泛滥无度的膜拜,比之泽被后世的人物所获的功名,实在赏不当功。
所以,雨果说“最伟大者乃是那些令世界展开笑颜的人”,可谓言之成理。尽管演员死后会迅速被公众淡忘——我不知道还有哪种职业可以夸口说比
演戏更受欢迎。这一切似乎足以证明戏剧之于人类的不可或缺。
那么,由此可以推导出什么顺理成章的结论呢?让我们看看:
我们拥有一群受众——从四面八方会聚一堂(或成群结队而来),友好而且通常抱有善意,事先已经准备好包容舞台上的缺憾与纰漏。他们事先掏了钱,也打算相信你将要告诉或展示给他们的一切。他们渴望精神食粮,渴望一点儿高于现实的生活;他们希冀在两三个小时的演出中,戏剧能够将心比心,不负他们的期待。
你不认为戏剧对这些全心信托的人们负有严肃的道德义务吗?——戏剧行业的每一个从业者,从舞台工作人员到大明星,都必须倾尽全力来解决创造性戏剧所面临的一切问题。
在结束这番关于戏剧观众的闲谈之前,我想就演员与观众在演出期间的特殊关系说几句话。就像所谓的“循环论证”#pageNote#0,演员越是能够化身为角色,“活在角色里”,观众所给予的反响就越热烈,反之亦然——公众越激动、越热情,演员的表演越是如有神助。有一条神秘的无形纽带把观众和舞台系在一起,让我们得见真正有灵感和创造性的演出。明乎此,就知道为什么把一台演出连看两场,你可能会这一场看得入神,下一场却心生不满和厌倦。
我曾跟奥蒂斯·斯金纳在全国巡演《桑丘·潘沙》(SanchoPan
za),#pageNote#1我一直记得他说过的话。在对观众的谢幕致辞里,他间或会感谢他们的精彩表演。此语乍听有些牵强,其实不然,因为一出戏能够大放异彩,也有观众的一半功劳。如果脚灯另一侧的每一个人都掌握了这个小秘密,单调的、毫无灵气的表演就会大大减少。
关于演员与观众之间这种相互作用的纽带的最惊人的例子,是我在俄国与莫斯科艺术剧院合作时见到的。这一著名演出团体的主顾对剧院及其演员抱有一种深挚的、近乎虔诚的态度。在演出中,死一般的沉寂笼罩着观众席。如果一幕戏正在进行,迟来者压根儿无意就座,而是耐心地在走廊上等待幕间休息。另一方面,演员对观众也是关怀备至。舞台上的小玩笑,哪怕在一流的商业剧院也很常见,在此地却闻所未闻。每一位演员都明白,假若片刻前自己还在侧幕讲滑稽故事或者谈论球赛,此刻他就不可能奉上情感饱满、生气勃勃的表演。同样,这里也存在着一条不成文的后台法则,即在开幕之前的半个小时,演员在后台必须化好装,缄口不语,安静地坐在演员休息室或者化装间里,“集中注意力”,或者借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述——“进入他们的圈子”#pageNote#2。如果有人在此刻向他们提问题,他们要么不明所以,要么冷脸相待。
《聪明误》(WoefromW
it)#pageNote#3。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扮演主人,他询问扮演一名客人的执法官(当时客串龙套角色),对由卡恰洛夫#pageNote#4饰演的男主人公的精神状态怎么看。执法官误以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问的是卡恰洛夫的表现,于是天真地回答说,卡恰洛夫很紧张,因为大公坐在台下观看演出。演出结束之后,执法官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着实教训了一顿,因为他在舞台上给出了与这出戏无关的回答。
在他们心中,剧院就是神殿。我没见过任何人在跨进后台入口时不脱帽——就像人们永远不会想着去教堂顺便聊聊天,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们也不会想到来剧院不为艺术还能为什么。如果某位演员来到剧院正赶上一场排练,哪怕是由演员们自己组织的私下排练(在商业剧院这种事是闻所未闻的),他也会蹑手蹑脚地走进观众席,安静地坐下来,观看同事们工作。
有些事例表明,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们的狂热非同一般。在国内战争期间,莫斯科燃料极为匮乏,夜间留在桌上的一杯水,早上会结成冰,除了革命领导者们不多的几栋住房之外,莫斯科唯一有供暖的建筑就是莫斯科艺术剧院。剧院的某次会议结束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主动提出,演员们可以睡在他们的化装间里,然而得到的是众口一词的回绝。剧院有如教堂,可不是一个睡觉的地方。结果导
致一位女主演科雷涅娃在自己的公寓里染上肺炎,不幸离世。#pageNote#5
几周后,莫斯科城下红军与白军鏖战,炮火纷飞,在所有建筑纷纷被劫掠、充公,或者被炮弹炸毁的情况下,双方之间还有一份心照不宣的默契:保护“他们的剧院”。剧院两侧设立了警戒线,此间的一切毫发未伤,没有一枚炮弹飞往那个方向。这是戏剧观众达成了共同的协议,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