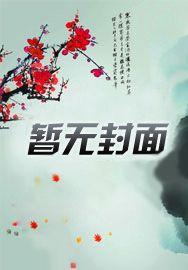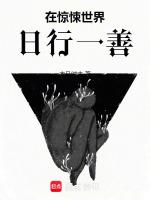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华夏真相集TXT > 第四十六集 敬业反武(第4页)
第四十六集 敬业反武(第4页)
徐敬业不从,对李思文道:叔父既阿附于武氏,应改姓武。
润州司马刘延嗣乃是刘审礼从弟,兄弟两个皆都是唐朝耿耿忠臣,亦不肯降。徐敬业将欲诛之,魏思温求免,命与李思文一起监押。
曲阿令尹元贞领兵来救润州,被徐敬业擒获,不肯屈服被杀。
武则天闻报,怒发如狂。诏命追削李世勣父子官职封爵,掘墓砍棺,复其本姓徐氏。复下诏旨,催令李孝逸进军平叛。
此时叛军局势,徐敬业亲率主力南渡长江,以略常、润二州,令唐之奇率部守卫江都;徐敬猷领兵五千人攻打和州;尉迟昭部攻打盱眙。
徐敬业攻陷润州,复还兵北上,屯兵高邮下阿溪;命弟徐敬猷率兵进逼淮阴,别将韦超、尉迟昭屯兵盱眙之南都梁山;布成犄角之势,以抵抗李孝逸三十万大军。
李孝逸率军抵达临淮,立派偏将雷仁智渡江,向徐敬猷发动进攻。
雷仁智不是徐敬猷对手,初战失利,退回江北。
李孝逸闻讯大惧,乃谓众将:我父当年曾随英国公西击突厥,曾云徐懋功用兵之能天下第一,号为军神。今逢其孙,亦是家学渊源,雷仁智果然难敌!
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身为监军,向李孝逸慷慨陈辞:天下安危,在兹一举。四方承平日久,忽闻狂狡,注心倾耳以俟其诛。今大军久留不进,远近失望,万一朝廷更命别将以代将军,则将军何辞,以逃逗挠之罪乎!
李孝逸见其所言有理,便命麾军渡江,并遣副将马敬臣引军往救盱眙。
马敬臣引军突至盱眙,下令攻进击,初战告捷,斩杀叛将尉迟昭、夏侯瓒等,随即进抵都梁山下。
徐敬业部下大将韦超拥兵占据都梁山,据险以守抵挡唐军,马敬臣无法前进,遣使往大营要求添兵再战。
李孝逸召集将佐,商讨作战方案。多数部将进言:韦超凭依险要自守,我步军无法施展其勇,骑兵亦不能展足奔驰;且穷寇皆拼死以战,若要强攻,士卒伤亡必大。不如分兵围困,大军直指江都,覆其巢穴为上。
支度使、广府司马薛克构言道:我谓诸公之论不然。韦超虽据险要,但其兵不多。我若多留兵围困,则前军兵力分散,少留兵则终遗后患。不如尽全力拿下都梁,淮阴、高邮之敌,则必望风瓦解矣!
李孝逸不决,又问魏元忠意见。
魏元忠道:可先击徐敬猷。
诸将皆道:有道是擒贼先擒王,不如先进攻徐敬业。徐敬业失败,则徐敬猷可不战而擒;若进攻徐敬猷,则徐敬业发兵来救,我将腹背受敌矣。
魏元忠笑道:我谓不然。敌之精兵集于下阿,仓卒聚集而来,利在决战;我军迎其中军,若万一失利,大事去矣!徐敬猷虽谓出身将门,乃战神之孙,但生性好赌,不习军事,且兵力单薄,军心极易动摇。我以大军进逼,旋即可破。徐敬业虽欲救之,远水难救近渴,不可及也。我军摧毁徐敬猷,然后乘胜而进,徐敬业虽有韩信、白起之能,亦不能当。今诸公欲舍弱而攻其强,绝非上策。
李孝逸终纳薛克构及魏元忠之议,北自率引大军,向都梁山杀来。
兵至山下,李孝逸下令围住山口,三面发起进攻。
唐军苗力登山,仰射以进,杀死叛军数百人,山上军心动摇。复经过半日激战,眼见红日西坠,残阳如血;韦超大败,连夜弃山逃走。
李孝逸既克都梁,引军继续东进,乘胜进攻淮阴,果然轻易取胜。
徐敬猷不敢支吾,只得放弃淮阴,脱身逃走。李孝逸下令歇兵一夜,来日复引大军南下,乘胜进逼高邮,来寻徐敬业主力决战。
徐敬业闻说都梁山及淮阴皆失,只得凭借下阿溪固守,与唐军主力形成对峙。
李孝逸遂派后军总管苏孝祥率兵五千,以小舟乘夜渡溪,向叛军发起进攻。
徐敬业早有防备,以逸待劳,且据地势之利,对唐军半渡而击。结果官军大败,苏孝祥战死,士卒淹死过半,左豹韬卫果毅成三郎遭俘。
叛军获胜,将成三郎擒献主帅徐敬业。成三郎威武不屈,立而不跪。
徐敬业刚要问来者为谁,身侧左长史唐之奇忽生一计,乃高声对诸将道:此人便是敌军主帅李孝逸。其为李唐宗室,却助武氏为虐,可即杀之,将首级号令三军。
诸将闻说擒了李孝逸,无不欢欣鼓舞。
成三郎大喊道:我是果毅将军成三郎,并非扬州道大总管李将军。我死何惧?为朝廷而死,妻子蒙受荣耀!然官军已至,尔等覆亡就在眼前,妻子籍没为奴,终不如我也。
叛军诸将闻此,复又丧气。徐敬业大怒,命将成三郎斩首示众。
苏孝祥逃回大营,来向主帅请罪。李孝逸惊恐不已,再次打算撤退。
监军魏元忠与行军管记刘知柔齐出劝谏,并献计道:今值隆冬,西北风大盛,芦荻干燥,又叛军战船营寨皆在南岸,我可顺风纵火,必可一战而决。
李孝逸闻言大喜,接受二人建议,调遣诸将,令各率领本部军马全线出击,发起火攻,顺风焚烧叛军营寨。
徐敬业军布阵已久,士卒疲倦观望,战阵不整,甫经火焚,顿时四散惊逃。
李孝逸进击,大败徐敬业,斩首七千,溺死者不可胜数。
徐敬业轻骑逃入江都,复带妻子儿女投奔润州,准备从海路逃往高丽。
李孝逸不给叛军喘吸之机,迅速进兵屯驻江都,分别派遣各将追击败残。徐敬业率残部行至海曲(江苏泰州)地界,正欲乘船出海,但受大风所阻。(本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