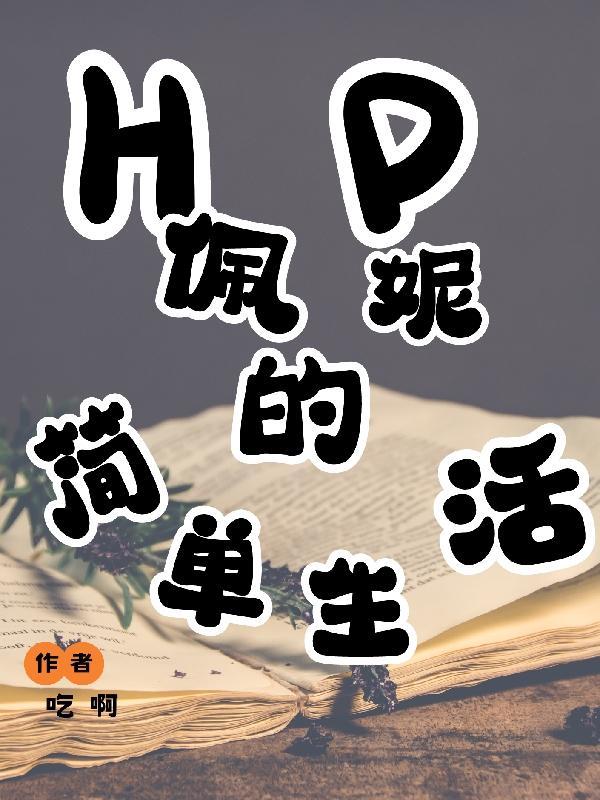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古代小妾有嫁妆吗 > 第19章 摇尾乞怜(第2页)
第19章 摇尾乞怜(第2页)
待倪姷带着白降和李武到达花园凉亭处时,果真如郭权所说,备上了茶点。
在一旁侍候茶水的,竟然是柳氏,只是这柳氏的脸色,瞧着倒是怪僵硬的。
倪姷瞧了她一眼,郭权继续笑,解释道:“回禀姨娘,柳通房是都督吩咐的。”
倪姷也笑,“都督费心了。”
“姨娘客气了。”郭权说完便带着柳氏退远了些。
“坐吧。”倪姷说完阖目了两息时间,又道:“声量低些,他们听不见。”
时傹这是怕来人会武,所以监视人的暗卫都离得远。
李武在倪姷对面落座,压低声音恭敬道:“主子,从与西凉接壤的边陲始,粮食已然开始涨价了,咱们可要跟着涨?”
倪姷端起茶盏抿了一口,淡淡道:“跟着涨。必要时候,能压便压一压,吃不起粮的人实在太多了。囤粮却不能停,陈粮总比无粮好。”
李武点头,又询问道:“是。只奇怪的是如今粮价已然不稳,朝昌与边陲之处的互市,竟是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西域的琉璃,南靖的玉瓷,万晋的鱼尾绫纱皆稳赚不赔,甚是稳妥。”
倪姷勾起唇笑了笑,意味深长道:“咱们不过是可以被上头那些人两指轻捏便能碾碎的蝼蚁。
他们只管过他们的富贵日子,粮价怎么涨于他们来说都是牛九一毛,他们何曾在乎过?
边陲之地过得再水深火热,只要传不到朝隍,他们都可以装聋作哑,粉饰太平。
我等着那一日,等着他们有朝一日手握偌大权柄和万贯家财,却买不到一粒粮食时。
等着他们跪到我面前,摇尾乞怜。”
闻言,白降,李武深深颔。
“主子吩咐的事,属下一定办好。”
倪姷站起身,环顾四周,语调不见一丝起伏,“待年关一过我入朝隍之后,吩咐许家,赵家,齐家朝倪家动手,连你手里的一起拿掉一些。
动静小些,不要惹眼。”
李武起身再次颔,“是,属下记下了。主子,朝隍城内一切已准备妥当,您可随时撤出。”
倪姷回身睨着他,笑道:“还不急。
待春闱过后,你也去一趟朝隍吧,你儿子得了廊州举人,春闱后你们一家人见一见,日后你妻子便留在你身边。”
闻言李武诧异地抬起头,随即眼眶含泪,“主子。。。。。原来主子藏了他这么些年,是。。。。
属下,多谢主子!”
倪姷神情散漫,语调含笑,“别,我藏着他,也是为了防李叔你。
谁知他也是个成器的,跟着你他不过是个商贾,跟着我,我给他换个身份,他就能是官。
其中得失利益,你心知肚明。”
听得这话,李武也不生气,笑着抹了一把眼泪,“经了那些事,主子心中有结属下也是明白的。
他能有如此造化,属下也知定是主子废了心思为他延请名师,属下和荆妻皆对主子感激不尽!”
当年李武作为赵士的随行小厮,冒着爱妻幼子被囚的危险,朝倪姷告赵士判主。后来他是亲眼瞧着赵士是怎么死的。
主子从他身边带走爱妻幼子,他心里没有一日不在担忧惧怕,可是后来偶尔见着时,看着他们被照顾得无比精心,妻子瞧着都年轻了几岁,他便也不怕了。
如今孩子得了好的前程,他除了松了口气之外自是更加感激。
就当孩子外出游学便罢了。
“回去吧,我派人给你消息之后再动身,下一回让曼秋来见我。”
李武起身朝倪姷长揖一礼,“遵命,属下告退。”
瞧着李武走远,倪姷坐下又抿了一口茶,只是抬杯时还朝远处的柳氏,举了举杯。
白降把自家主子的动作放在眼里,只觉得主子好似是心情愉悦间顺便逗了逗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