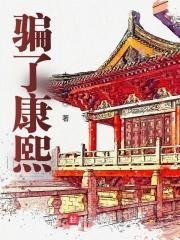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我欲为后八月薇妮免费阅读 > 第97章 第 97 章(第3页)
第97章 第 97 章(第3页)
虽然张相有心维护,可皇帝的交代,是让东厂听从田丰的号令指使,所以张相也有些无可奈何。
只能在看着江恒有些撑不过去的时候,才忙出言阻止。
私下里,张相询问江恒到底是做了什么,才让皇帝如此震怒。江恒只是苦笑。
他也问过田丰,但田丰学乖了,并没有泄露半分。
毕竟这种事若是传扬出去,没有人能讨得了好。田丰也必须在皇帝面前假装一无所知。
因为此事是太后用一种很巧妙的手段传给皇帝知道的。
那天太后在从田丰口中得知后,田丰本以为太后会立刻让他去禀告皇上。
谁知太后并没有如此吩咐,反叫他守口如瓶。
后来田丰想通了,毕竟皇帝最恨此事,如果是他去告诉皇帝,非但马屁拍不到,反而会给踢掉脑袋。
而太后的安排,也让田丰大为震惊,震惊之余又极为佩服。
那天,宝鸾公主提了那只皇帝所赏赐的白玉鹦哥去养心殿。
皇帝见小公主来到,勉强露出几分笑意。
又见她带了鹦哥,便道“你拎着他来做什么。”细看那鹦哥,比当初带走的时候好像又长了好些,可见宝鸾喂养的十分精心。
宝鸾行了礼,道“听说父皇近来有些烦心,宝鸾特意带了鹦哥给父皇解闷。”
皇帝笑道“怎么,难道他又学会了什么新鲜的诗句”
宝鸾道“儿臣不大教他诗句,他渐渐地把父皇之前教的都要忘了。只会学人说话。”
皇帝道“是吗”一时玩心乍起,便去逗弄那鹦哥“你把和玉的那句诗也忘了吗”
鹦哥在笼子上走来走去,喉咙里嘀嘀咕咕,听皇帝说了这句,才突然道“和玉,和玉”
正嘉听他口齿伶俐,不禁大笑“说的好。那诗呢”
宝鸾也道“小白,快念诗给父皇听。”
鹦哥目光炯炯地看着人,过了会儿,没有念什么诗,反而叫道“江指挥使”
“江”皇帝先是还带着笑,但是慢慢的,那笑影就在脸上凝固了。
他转头看看宝鸾“怎么,你还教他这个了”
宝鸾乖乖回答“儿臣没有教,只是有时候带他去云液宫,也许是在路上或者哪里学会了的。”
那天,宝鸾公主离开养心殿的时候,那只白玉鹦哥却仍是留下了,再后来,这鹦哥就自宫内消失不见了。
皇帝是个最精明不过的人。
这白玉鹦哥有时候不必人教,但别人说的话,他也会留心,暗暗学会了。
宝鸾虽然说她带了鹦哥去云液宫,路上可能听见人叫江恒,但也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在云液宫里。
再加上先前田丰提起,云液宫拗断脖子而死的小太监死状有些可疑。
这看似草蛇灰线般的线索,已经足够皇帝心明如镜了。
最终张相实在是看不过,拦住田丰道“主子再怎么恼他,也没说要弄死他,以后兴许还会在御前当差,你何必这样不留情面”
田丰道“主子之所以派了我来帮你,就是怕你心慈手软下不去,你连这个都不明白”
张相当然明白,但却也有些于心不忍“总之,这是东厂,不是你号施令的地方,你若想告状,便去主子面前告我今儿却不许你再动手了”
田丰气的将手中的鞭子扔下“你以为他真的还能出去告诉你,他犯的是死罪,你既然想袒护他,那你且等着。”
张相哼道“等着就等着。”
若换了以前,张相自也不大敢这样跟田丰对呛,但如今毕竟郑谷回来了,倒是让他心里有了个依仗似的。
田丰说罢,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
张相忙叫人把江恒放下,扶着他到旁边坐了,看他身上的鞭痕,道“江指挥使你到底做了什么打人眼睛的事,要用这种狠手若不是我盯着,只怕会要了你的命。”
江恒笑道“没什么,东厂又不是吃饭的地方,能囫囵进来囫囵出去的毕竟少。”
张相叹了口气,叫人去取伤药给他敷了。
如此又过了两天,正嘉一直都没有吩咐如何处置。
直到这一日,有一个本来绝对不会出现在东厂的人突然驾临了。
江恒因为染了病,整个人咳嗽不停,头晕眼花,抬头看见来人,一时却竟没有认出来。
直到那人在他跟前又站了半晌,江恒才总算清楚,便笑道“是你。怎么竟换了一身打扮了难不成是还俗了”
这来者竟是萧西华。
但是西华并不是穿着道袍,而是一身暗蓝色的缎袍,头上金冠束顶。整个人从头到脚都贵气十足,令人肃然起敬。
萧西华道“江指挥使,你相不相信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