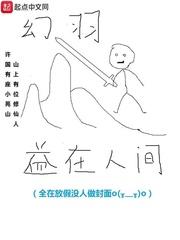三七小说网>恶毒女配性别男 > 第76章 金鸡山其四(第3页)
第76章 金鸡山其四(第3页)
云研心知自己辜负了姜无岐对他的保护,满面歉然地道“子恒不在了,子恒的家人尚在,我不愿见他们惨死。”
“你此举与寻死无异。”姜无岐沉声道,“你带上止血疗伤的草药,贫道送你去与余下之人汇合。”
云研慌忙问道“子恒的家人可是安好”
姜无岐回道“子恒的幼妹安好,子恒旁的家人贫道不识得。”
待云研急匆匆地将草药塞入药箱,姜无岐即刻提起云研的后襟,飞身赶往毓秀镇最大的那处宅子。
姜无岐一进得那宅子,便有人急切地问道“外头如何了,我家的庄稼如何了”
被这人一提醒,不少人纷纷围了上来
“我家的古董应当没碎罢。”
“我家的宅子可千万别被毁了。”
“老朽藏在枕下的一锭银子不知还在不在”
“道长,你且行行好,去看看我那口棺材是否无事。”
“道长,我那小女儿,我那小女儿还在家中,你快些去救一救罢。”
不多时,姜无岐面前竟是跪了一地。
姜无岐并不理会其他人,只朝那妇人道“你稍待,贫道这就去救你那小女儿。”
他说罢,不作停留,飞身而去,独留云研。
众人适才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姜无岐身上了,大抵是要姜无岐护住他们的财物,并未有一人注意到云研。
现下姜无岐一走,他们终是注意到了云研,俱是一脸不屑。
云研在人群中穿梭,众人视他如蛇蝎,他一靠近,便散了去。
这反倒为云研了便利,云研轻易地便从人群中寻到了子恒的家人。
他们瞧来狼狈,但算得上完好,只子恒的幼妹手上有些许擦伤。
云研不顾她的挣扎,强行为她将手包扎妥当,她却是厌恨地啐了云研一口,又将手上的细布扯了去,弃于地,踩了又踩。
云研抹去面上的唾沫子,不徐不疾地行至墙角,坐下,后又淡然地道“我带了伤药,你们若有受伤的,可来我处医治。”
半晌,无人应声。
云研将自己足上的伤包扎妥当,便闭目养神,照常思念着已过世三年有余的子恒。
他的子恒待他极好,在他失怙失恃之时陪伴在他身侧数个昼夜,在他表明要学医之时,更是偷偷地将家中的五颗鸡蛋塞入了他手中,还一脸肯定地道他必然能成为一代名医,他笑着质疑,子恒却一本正经道自己是铁口直断,所言必定成真。
如今他还在,为何子恒却不在了
是他,是他把子恒害死了。
一刻钟后,才有一人熬不住疼,抱着鲜血淋漓的手,行至他面前,命他为其包扎。
包扎完毕后,那人又自然地与旁人一道中伤他。
他无暇去听闲言碎语,自顾自地思念着他的子恒。
又过了片刻,姜无岐抱着三个孩童回来了,三个孩童哭叫连连,蹭了姜无岐一身的涕泪。
姜无岐放下三个孩童,耳中听得些对云研的中伤,望了眼那些中伤云研之人,语调平淡地道“你们不及他。”
言罢,他唯恐他们暴动起来,伤了云研,便又为云研划了一个结界。
而后,他便步出了大宅子,外头是破晓时分,雄鸡一唱,天光大亮。
他仰望着初生的朝阳,低声道“酆如归,你那边的天可是也亮了”
思及酆如归,他心口生疼,他明明只受了些轻伤,却顿觉浑身上下无一处不疼。
酆如归合该在他身畔才是,由他纵容着,由他安慰着,由他身上吸食血液。
酆如归那瘾倘使已然作了,定会自残,待他实在撑不住了,许会另寻一人,他会伏在那人身上,抱住那人,吸吮那人的肌肤,小心翼翼地咬开一个破口,吸食血液,在吸食过后,他会歉然地舔舐那人的伤口,任凭那人摩挲他的腰身,一如吸食他的血液之时一般,他甚至会褪尽衣衫,供那人查看他身上的伤痕。
也许他于酆如归而言,并无不同。
他生性无趣,酆如归能忍受他良久,全然是因为他会在酆如归受不住那瘾之时,主动送上自己的血液罢
他心乱如麻,连有一头花豹近身也不曾察觉,直到被扑倒在地,咽喉险些被咬,他才勉强清醒过来,击毙了花豹。
毓秀镇东面、北面皆是绵延的崇山峻岭,飞禽走兽无数,不知其中被怨气所感染的有几何
姜无岐定了定神,催动拂尘,逼近近侧的飞禽走兽,大开杀戒。
一条条生命从他手中流逝,纵然它们已无药可救,但依旧是鲜活的生命。
他足下是接连倒下的尸身,他面上覆上了猩红的血液,连累他眼中的阳光变作了猩红。
与酆如归那瘾作得厉害之时,双目生出的猩红是一般颜色。
他须得快些赶到酆如归身边去,但酆如归身在何处酆如归是否早已不需要他了请牢记收藏,&1t;